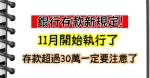4/4
下一頁
大宋第一全才:科學的巨人,道德的矮子?

4/4
▲宋神宗趙頊畫像。圖源:網絡
事實上,沈括引起王安石的強烈不滿和詆毀,是因為沈括剛好在王安石罷相期間,對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異議。
比如新法里有一條「戶馬法」,規定與遼國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養馬,一旦兩國發生戰事,這些馬要被徵召為官馬,用於抵禦遼國的騎兵。然而,沈括經過考察後,指出這條政策有很大的問題:遼國的戰馬是常年打仗打出來的,而我們的戰馬是老百姓豢養出來的,真遇上戰爭,這些馬能行嗎?
問題在於,王安石在位的時候,沈括沒說,王安石罷相後,他才說這個政策有問題。在王安石看來,沈括這種行徑,不就是一個反覆的小人嗎?
跟戶馬法一樣,沈括以科學家嚴謹的眼光,發現了免役法的問題。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不久,沈括給新宰相吳充上書,指出免役法的弊端。免役法同樣是新法的重要內容,規定所有人出錢代替原來的服徭役。但沈括髮現其中有個問題,窮戶原來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鋪開後,他們也要交錢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書吳充,希望能修正這個問題,免去窮戶納役錢的負擔。
可以看出,沈括對新法的批評都很有針對性,也很到位。但這在新黨內部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以攀龍附鳳起家的新法主力之一蔡確,給宋神宗上了個摺子,說沈括看到王安石罷相,擔心政治風向有變,所以「前後反覆不同」,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力保自己處於不倒之地。
另一名新法核心人物呂惠卿,此時也公報私仇,大肆打擊沈括。連宋神宗都說,呂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可見呂惠卿在詆毀沈括上也是不遺餘力的,新黨內部的權斗十分酷烈。
在新黨內部的傾軋下,沈括最終從三司使任上,被貶為宣州知州。
我們現在復盤沈括與新黨幾個核心人物的關係,可以明確沈括被排擠至少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新黨人物普遍器量小,難以接受哪怕是內部人對新法政策的任何批評和修正意見。這也是新法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則是沈括自身的原因,他選擇在王安石罷相後對新法發出非議,難免給人落下保全自身、巧為身謀的非議,但其實,這只是一個性格懦弱而有良知的官員在當時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罷了。王安石對新法相當固執己見,不能容忍不同意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沈括性格則偏於懦弱,不願捲入對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當政時避免與之發生正面衝突,事後出於良知,採取委曲求全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應該說,沈括這種人並不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但也絕不是王安石等人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個內心相對懦弱、不敢跟同僚正面硬剛的好人。這與他面對外交和軍事上敵人那種強硬而不怕死的態度,正好形成了反差。有些人就是不擅長處理同事關係,很可惜,但沒辦法。
與蘇軾的關係,更是成了沈括身後之名的「夢魘」。
本質上,沈括和蘇軾是同一類人,面對新舊兩黨圍繞變法展開的權斗,他們更願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處於哪一個陣營,都曾對新法提出過批評。
區別在於,蘇軾是一個勇敢的批評者,面對問題,他會隨時站出來,懟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說,他是一個懦弱的批評者,不敢正面硬剛。
可是,處於同一時代的這兩個人,卻因為「告密事件」而使兩人的關係蒙上濃重的陰影。
根據宋人王銍《元佑補錄》的記載,熙寧七年(1074年),沈括奉命察訪兩浙農田水利期間,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敘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簽帖以進,雲詞皆訕懟」。意思是,沈括跟蘇軾要了新近寫的詩,回京後研讀,並一一標註出詩中誹謗新法的地方,然後進呈給皇帝。
王銍說,5年後,元豐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獄構陷蘇軾,製造烏台詩案,「實本於(沈)括」,正是跟沈括學的。
所謂「告密事件」雖然沒有對蘇軾造成不好的影響,但由於記述者將歷史事件進行前後關聯,導致沈括在後世的形象背負了嚴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針對「告密事件」是否真實存在,史學家向來有不同說法。南宋史學家李燾寫《續資治通鑑長編》,雖然引述了王銍的記載,但專門附註說,此事恐有問題,「當詳考」。而事件的兩個當事人——沈括和蘇軾,都沒有關於「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來。從蘇軾的詩文看,蘇軾與沈括的唯一交往發生在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從杭州回京路過潤州時,沈括送給他一塊從延州得來的石墨,蘇軾於是寫了《書沈存中石墨》記下來。蘇軾當然是一個大度、不計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確實曾發生過「告密事件」,他真的會連提都不提一下嗎?
另一個反證的例子是,沈括終生與李之儀關係密切。李之儀是蘇軾的鐵粉,與蘇門中人交從熱絡。在蘇軾被貶海南之時,平時門下客唯恐受牽連,紛紛斷絕與蘇軾的關係,唯有「端叔(李之儀)之徒,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可見李之儀為人的正派,以及對蘇軾的情義之深。
這樣一個人,對沈括同樣十分尊重。李之儀一生輾轉為官,始終把蘇軾、沈括等人的畫像帶在身邊。沈括去世時,遠在甘肅做官的李之儀面對沈括畫像,作《沈存中畫像贊》,遙祭亡友。他說沈括是「一世絕擬」,「凜然孤風」,評價那是相當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儀這個愛恨鮮明的蘇軾鐵粉,還會對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嗎?
我們習慣對歷史上的任何記載,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從未想過這些記載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記述者的道聽途說。殊不知,這種廉價的接受,對於歷史當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毀滅性打擊。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連當代名聲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辭鑿鑿地說,沈括就是一個告密小人,並妄加推測說,沈括之所以這麼做,純粹是妒忌蘇軾的才學。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真的太難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從有」的文化氛圍中,「坐實」了他就是一個熱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唉,沈括的悲劇,部分是其性格造成的,但誰說歷史和時代就沒有責任呢?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終為他的仕途畫上了句號。
元豐五年(1082年),在升任龍圖閣學士僅僅半年多後,鄜延經略使沈括就因永樂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問罪,被撤職查辦,並安置於隨州(今湖北隨縣)。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結束。
靈武之役後,沈括、種諤建議朝廷經營橫山,築壘蠶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為寇。宋神宗於是派給事中徐禧作為欽差大臣,前往鄜延負責築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築古烏延城的提議,力言先築永樂城。沈括起初不贊成,認為永樂距離後方太遠,恐怕孤立無援。徐禧不聽。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選擇了妥協,一切由徐禧專決。
結果,永樂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軍二萬五千人,「得免者什無一二」,傷亡慘重。永樂被圍時,沈括正護守米脂,所部僅萬人左右,在進援受阻的情況下,受詔退保綏德。事後,作為一路之帥的沈括以「措置、應敵俱乖方」而問罪,形同流放。
還是那句話,有些人對敵人強悍勇敢,但對熟人(包括同事、親人等)態度軟弱。沈括一生吃虧在這裡,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繼室張氏經常惡語辱罵沈括,是個十足的「河東獅」,有時甚至拳腳相加,據說還將沈括與前妻所生的兒子趕出家門。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讓而已。
他認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繼位,大赦天下。沈括遇赦從隨州改授秀州(今浙江嘉興)團練副使,雖然仍無自由遷居的權利,但他已經感到很高興。因為秀州鄰近他的家鄉杭州,比起之前「三年無半面之舊」,如今「一日見平生之親」,他覺得相當幸運了。
早在熙寧九年(1076年),沈括就奉命編繪《天下州縣圖》,但後來由於軍政事務繁忙,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完成這件事。遭到貶謫後,他終於有大把時間,以堅韌的毅力去編繪《天下州縣圖》。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前後歷經12年之後,沈括總算編訂完成《天下州縣圖》,以待罪者的身份獲朝廷特許到汴京(開封)進呈這一圖卷。宋哲宗賜絹百匹,准許沈括在秀州境內自由行動。
《天下州縣圖》是當時最為精確的地圖,大大提高了古代中國繪製地圖的科學性。可惜後來的南宋,戰亂頻發,《天下州縣圖》也毀於戰火之中,成為千古遺憾。
沈括進呈《天下州縣圖》的第二年,元祐四年(1089年),沈括獲准自由遷居。接到詔命後,沈括舉家搬遷至早年在潤州(今江蘇鎮江)購置的夢溪園,在此隱居,直至紹聖二年(1095年)病逝,享年65歲。
在夢溪園,沈括度過了人生最後的6年時間。用他自己的話說:「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在與筆硯對談、回憶往事的最後歲月,沈括寫下了不朽的傳世著作——《夢溪筆談》。
歷史學者祖慧在論文中如此評價沈括:
沈括是一位具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工作認真務實、能夠體恤民情的良吏,但他卻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具備政治家應有的膽識與果敢堅毅。他學識淵博,機敏過人,但面對權力鬥爭與矛盾衝突卻顯得無所適從。他遇事總是退讓、妥協,希望能委曲求全,卻總是陷入更深的困境,遭到王安石及變法派的疏離與攻擊。這就是沈括。
對於沈括而言,從元豐五年(1082年)遭貶謫以來的13年,是他一生最鬱悶的時光。但對歷史而言,它讓一個不擅長人際關係的懦弱官員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從而還給了後世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個人的不幸,卻是歷史的幸運,這正是時代的弔詭。
事實上,沈括引起王安石的強烈不滿和詆毀,是因為沈括剛好在王安石罷相期間,對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異議。
比如新法里有一條「戶馬法」,規定與遼國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養馬,一旦兩國發生戰事,這些馬要被徵召為官馬,用於抵禦遼國的騎兵。然而,沈括經過考察後,指出這條政策有很大的問題:遼國的戰馬是常年打仗打出來的,而我們的戰馬是老百姓豢養出來的,真遇上戰爭,這些馬能行嗎?
問題在於,王安石在位的時候,沈括沒說,王安石罷相後,他才說這個政策有問題。在王安石看來,沈括這種行徑,不就是一個反覆的小人嗎?
跟戶馬法一樣,沈括以科學家嚴謹的眼光,發現了免役法的問題。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不久,沈括給新宰相吳充上書,指出免役法的弊端。免役法同樣是新法的重要內容,規定所有人出錢代替原來的服徭役。但沈括髮現其中有個問題,窮戶原來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鋪開後,他們也要交錢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書吳充,希望能修正這個問題,免去窮戶納役錢的負擔。
可以看出,沈括對新法的批評都很有針對性,也很到位。但這在新黨內部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以攀龍附鳳起家的新法主力之一蔡確,給宋神宗上了個摺子,說沈括看到王安石罷相,擔心政治風向有變,所以「前後反覆不同」,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力保自己處於不倒之地。
另一名新法核心人物呂惠卿,此時也公報私仇,大肆打擊沈括。連宋神宗都說,呂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可見呂惠卿在詆毀沈括上也是不遺餘力的,新黨內部的權斗十分酷烈。
在新黨內部的傾軋下,沈括最終從三司使任上,被貶為宣州知州。
我們現在復盤沈括與新黨幾個核心人物的關係,可以明確沈括被排擠至少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新黨人物普遍器量小,難以接受哪怕是內部人對新法政策的任何批評和修正意見。這也是新法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則是沈括自身的原因,他選擇在王安石罷相後對新法發出非議,難免給人落下保全自身、巧為身謀的非議,但其實,這只是一個性格懦弱而有良知的官員在當時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罷了。王安石對新法相當固執己見,不能容忍不同意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沈括性格則偏於懦弱,不願捲入對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當政時避免與之發生正面衝突,事後出於良知,採取委曲求全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應該說,沈括這種人並不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但也絕不是王安石等人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個內心相對懦弱、不敢跟同僚正面硬剛的好人。這與他面對外交和軍事上敵人那種強硬而不怕死的態度,正好形成了反差。有些人就是不擅長處理同事關係,很可惜,但沒辦法。
與蘇軾的關係,更是成了沈括身後之名的「夢魘」。
本質上,沈括和蘇軾是同一類人,面對新舊兩黨圍繞變法展開的權斗,他們更願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處於哪一個陣營,都曾對新法提出過批評。
區別在於,蘇軾是一個勇敢的批評者,面對問題,他會隨時站出來,懟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說,他是一個懦弱的批評者,不敢正面硬剛。
可是,處於同一時代的這兩個人,卻因為「告密事件」而使兩人的關係蒙上濃重的陰影。
根據宋人王銍《元佑補錄》的記載,熙寧七年(1074年),沈括奉命察訪兩浙農田水利期間,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敘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簽帖以進,雲詞皆訕懟」。意思是,沈括跟蘇軾要了新近寫的詩,回京後研讀,並一一標註出詩中誹謗新法的地方,然後進呈給皇帝。
王銍說,5年後,元豐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獄構陷蘇軾,製造烏台詩案,「實本於(沈)括」,正是跟沈括學的。
所謂「告密事件」雖然沒有對蘇軾造成不好的影響,但由於記述者將歷史事件進行前後關聯,導致沈括在後世的形象背負了嚴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針對「告密事件」是否真實存在,史學家向來有不同說法。南宋史學家李燾寫《續資治通鑑長編》,雖然引述了王銍的記載,但專門附註說,此事恐有問題,「當詳考」。而事件的兩個當事人——沈括和蘇軾,都沒有關於「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來。從蘇軾的詩文看,蘇軾與沈括的唯一交往發生在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從杭州回京路過潤州時,沈括送給他一塊從延州得來的石墨,蘇軾於是寫了《書沈存中石墨》記下來。蘇軾當然是一個大度、不計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確實曾發生過「告密事件」,他真的會連提都不提一下嗎?
另一個反證的例子是,沈括終生與李之儀關係密切。李之儀是蘇軾的鐵粉,與蘇門中人交從熱絡。在蘇軾被貶海南之時,平時門下客唯恐受牽連,紛紛斷絕與蘇軾的關係,唯有「端叔(李之儀)之徒,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可見李之儀為人的正派,以及對蘇軾的情義之深。
這樣一個人,對沈括同樣十分尊重。李之儀一生輾轉為官,始終把蘇軾、沈括等人的畫像帶在身邊。沈括去世時,遠在甘肅做官的李之儀面對沈括畫像,作《沈存中畫像贊》,遙祭亡友。他說沈括是「一世絕擬」,「凜然孤風」,評價那是相當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儀這個愛恨鮮明的蘇軾鐵粉,還會對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嗎?
我們習慣對歷史上的任何記載,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從未想過這些記載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記述者的道聽途說。殊不知,這種廉價的接受,對於歷史當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毀滅性打擊。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連當代名聲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辭鑿鑿地說,沈括就是一個告密小人,並妄加推測說,沈括之所以這麼做,純粹是妒忌蘇軾的才學。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真的太難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從有」的文化氛圍中,「坐實」了他就是一個熱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唉,沈括的悲劇,部分是其性格造成的,但誰說歷史和時代就沒有責任呢?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終為他的仕途畫上了句號。
元豐五年(1082年),在升任龍圖閣學士僅僅半年多後,鄜延經略使沈括就因永樂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問罪,被撤職查辦,並安置於隨州(今湖北隨縣)。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結束。
靈武之役後,沈括、種諤建議朝廷經營橫山,築壘蠶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為寇。宋神宗於是派給事中徐禧作為欽差大臣,前往鄜延負責築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築古烏延城的提議,力言先築永樂城。沈括起初不贊成,認為永樂距離後方太遠,恐怕孤立無援。徐禧不聽。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選擇了妥協,一切由徐禧專決。
結果,永樂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軍二萬五千人,「得免者什無一二」,傷亡慘重。永樂被圍時,沈括正護守米脂,所部僅萬人左右,在進援受阻的情況下,受詔退保綏德。事後,作為一路之帥的沈括以「措置、應敵俱乖方」而問罪,形同流放。
還是那句話,有些人對敵人強悍勇敢,但對熟人(包括同事、親人等)態度軟弱。沈括一生吃虧在這裡,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繼室張氏經常惡語辱罵沈括,是個十足的「河東獅」,有時甚至拳腳相加,據說還將沈括與前妻所生的兒子趕出家門。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讓而已。
他認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繼位,大赦天下。沈括遇赦從隨州改授秀州(今浙江嘉興)團練副使,雖然仍無自由遷居的權利,但他已經感到很高興。因為秀州鄰近他的家鄉杭州,比起之前「三年無半面之舊」,如今「一日見平生之親」,他覺得相當幸運了。
早在熙寧九年(1076年),沈括就奉命編繪《天下州縣圖》,但後來由於軍政事務繁忙,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完成這件事。遭到貶謫後,他終於有大把時間,以堅韌的毅力去編繪《天下州縣圖》。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前後歷經12年之後,沈括總算編訂完成《天下州縣圖》,以待罪者的身份獲朝廷特許到汴京(開封)進呈這一圖卷。宋哲宗賜絹百匹,准許沈括在秀州境內自由行動。
《天下州縣圖》是當時最為精確的地圖,大大提高了古代中國繪製地圖的科學性。可惜後來的南宋,戰亂頻發,《天下州縣圖》也毀於戰火之中,成為千古遺憾。
沈括進呈《天下州縣圖》的第二年,元祐四年(1089年),沈括獲准自由遷居。接到詔命後,沈括舉家搬遷至早年在潤州(今江蘇鎮江)購置的夢溪園,在此隱居,直至紹聖二年(1095年)病逝,享年65歲。
在夢溪園,沈括度過了人生最後的6年時間。用他自己的話說:「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在與筆硯對談、回憶往事的最後歲月,沈括寫下了不朽的傳世著作——《夢溪筆談》。
歷史學者祖慧在論文中如此評價沈括:
沈括是一位具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工作認真務實、能夠體恤民情的良吏,但他卻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具備政治家應有的膽識與果敢堅毅。他學識淵博,機敏過人,但面對權力鬥爭與矛盾衝突卻顯得無所適從。他遇事總是退讓、妥協,希望能委曲求全,卻總是陷入更深的困境,遭到王安石及變法派的疏離與攻擊。這就是沈括。
對於沈括而言,從元豐五年(1082年)遭貶謫以來的13年,是他一生最鬱悶的時光。但對歷史而言,它讓一個不擅長人際關係的懦弱官員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從而還給了後世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個人的不幸,卻是歷史的幸運,這正是時代的弔詭。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