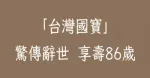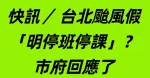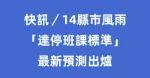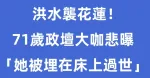3/3
下一頁
他手握十萬雄兵,對奪嫡冷眼旁,熬過三朝成乾隆最信賴的皇叔

3/3
他早年騎馬打獵時,腿上落下了病根,一到陰雨天就疼痛難忍。這囚室陰冷潮濕,一入秋,那條傷腿就開始變本加厲地折磨他。刺骨的疼痛從骨髓里鑽出來,常常讓他徹夜難眠。
但比身體上的痛苦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絕望。
他被自己最敬愛的父親拋棄,被曾經親近的兄弟陷害,轉眼之間,就從一個天之驕子,變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階下囚。
他整日整日地面對著那四麵灰色的高牆,從最初的憤怒、不甘,到後來的茫然、麻木。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想不通自己究竟錯在了哪裡。難道自己的赤誠忠心,在權力面前,就如此一文不值嗎?
時間一天天過去,他變得越來越沉默,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他覺得自己就像院子裡那棵在秋風中凋零的枯樹,正在一點點地死去。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十三阿哥即將被世人遺忘,爛死在這高牆之內時,一道微光,卻頑強地照進了他黑暗的世界。
在所有兄弟都對他避之不及時,只有四哥胤禛,沒有忘記他。
胤禛不敢公然違抗聖意,但他冒著觸怒康熙的巨大風險,想盡了一切辦法,偷偷地幫助這個落難的弟弟。
他不能親自前來,就派了自己最心腹的老太監,隔三差五地借著送雜物的名義,給允祥送來治療腿傷的特效藥、禦寒的衣物和一些可口的飯菜。更重要的,是那些外面根本看不到的書籍。
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老太監又一次悄悄地來了。這一次,他帶來了一件厚厚的、針腳有些粗糙的黑狐皮斗篷,還有一句話。
「王爺,這是四爺讓奴才給您帶來的。」老太監壓低了聲音,「四爺說,這斗篷是他福晉帶著府里的下人,趕了好幾天才做好的,讓您一定穿上,別凍著。四爺還讓奴才給您帶句話。」
允祥接過斗篷,觸手溫暖。他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這樣的暖意了。
「四哥說什麼?」他沙啞地問。
老太監湊到他耳邊,一字一句地複述:「四爺說,天冷了,讓你務必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允祥反覆咀嚼著這句話,眼中渾濁的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
在這被全世界拋棄的時刻,還有人記得他,還在為他籌謀,還在等著他。
這句話,像一道驚雷,劈開了他心中積鬱已久的絕望和麻木,讓他瀕臨崩潰的精神重新找到了支點。他不能倒下!他若是倒下了,豈不是正中了那些害他的人的下懷?豈不是辜負了四哥的一片苦心?
從那天起,允祥變了。
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沉浸於自傷自憐。他開始冷靜地反思自己過去的一切。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失敗,在於空有一身武勇,卻不懂權謀之術;空有一片赤誠,卻不懂人心之險。
他開始利用這漫長而無所事事的幽禁時光,瘋狂地讀書。胤禛送來的每一本書,他都如饑似渴地閱讀。從經史子集,到兵法謀略,再到錢糧水利這些他過去從不關心的政務文書。
這間小小的囚室,成了他的藏經閣,他的修煉場。
十年,整整十年。
他的人雖然被困在了這方寸之地,但他的思想和眼界,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和錘鍊。他從一個只懂騎射衝鋒的「莽夫」,逐漸蛻變成了一個深諳治國之道、洞察人性的「謀士」。
他對著斑駁的牆壁,用一根小樹枝,一遍遍地推演著戰局,分析著朝政。他仿佛在為未來的某一天,做著一場漫長而周密的準備。
十年幽禁,沒有摧毀他,反而磨礪了他。他就像一把被投入烈火中反覆鍛打的寶刀,褪去了所有的雜質,只剩下最純粹的鋒芒,藏於鞘中,靜待出鞘的那一天。
04
光陰似箭,日升月落。高牆之內的日子,漫長得像是沒有盡頭。
對於外面的人來說,十三阿哥允祥已經是一個被遺忘的名字。但在這間陰冷的囚室里,允祥卻為自己開闢了一個別樣的「朝堂」。
他每天的生活,變得極其規律。天一亮,就著窗戶透進來的微光,開始讀書。那些胤禛送來的書籍,已經快被他翻爛了,書頁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他的心得和批註。沒有紙筆,他就用燒完的炭條在地上寫劃;地寫滿了,就擦掉重來。
他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了一遍又一遍,將歷朝歷代的興衰成敗、權謀得失,都刻進了自己的腦子裡。他不再僅僅把自己當成一個皇子,一個將軍,而是站在一個帝王的角度,去思考那些複雜的政務。
國庫為何會空虛?漕運為何會淤堵?鹽政的弊端在哪裡?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如何解決?
這些過去他覺得頭疼又無趣的「俗務」,現在成了他每天研究的課題。他發現,治理一個國家,遠比打贏一場戰爭要複雜得多。光有匹夫之勇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的是細緻入微的計算和長遠的規劃。
腿上的舊疾,在潮濕的環境里愈發嚴重,疼起來的時候,像是無數根針在扎骨頭,冷汗能浸濕整件衣服。但他從不呻吟一聲,只是咬緊牙關,默默忍受。他把這份疼痛,當成了對自己意志的磨礪。
有時候,為了轉移注意力,他會在地上畫出大清的疆域圖,用幾顆石子代表軍隊,反覆推演著西北邊疆的戰局,思考著如何布陣,如何運送糧草。
起初,那些奉命看守他的侍衛,都帶著一種同情和輕視的眼光看他。他們覺得這個失勢的皇子,不過是在故作姿態,用讀書來打發絕望的時光罷了。可日子久了,他們臉上的表情,漸漸變成了敬畏。
他們想不通,一個人在毫無希望的十年囚禁里,為何還能保持如此驚人的毅力和專注。他不像一個囚犯,反倒像一個閉關修煉的絕世高手。
允祥與外界唯一的聯繫,就是四哥胤禛。
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而隱秘的交流方式。胤禛每次託人送來的東西,都藏著玄機。可能是一包藥材,包藥的紙上,用米醋寫著幾個不起眼的字,風乾了看不出來,用火一烤,字跡就顯現出來;也可能是一本書,在某頁的字裡行間,用一個微小的墨點做標記,對應著一句暗語。
通過這種方式,胤禛源源不斷地將外界的信息傳遞進來。今天哪個大臣被調動了,明天某個地方發生了水災,皇阿瑪的身體狀況如何,八爺黨又有什麼新的動向……
而允祥,則成了胤禛最隱秘、最可靠的「幕後軍師」。
他身在局外,沒有了利益的糾葛,反而能把很多事情看得更通透。他會用同樣的方式,將自己的分析和建議傳遞出去。
他提醒胤禛,刑部尚書某某看似中立,實則內心早已倒向八爺黨,需多加提防;他建議胤禛,在康熙面前,要多表現出對兄弟的友愛和對政務的勤勉,但切忌功高蓋主。
康熙五十七年,西北準噶爾部再次叛亂,朝廷急需一位能征善戰的將領出征。朝堂上,各派勢力都想推舉自己的人,爭論不休。胤禛通過暗語,將幾位候選將領的名單傳給了允祥。
允祥對著這份名單,在囚室里枯坐了整整一夜。他結合自己對兵法的研究和對這幾位將領過往經歷的了解,分析了他們的派系背景、性格特點和用兵風格。第二天,他只在送出去的食盒夾層里,藏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只有三個字:「保年羹堯。」
年羹堯當時雖然只是四川巡撫,但在胤禛的極力舉薦和運作下,最終被康博任命為撫遠大將軍,代替十四阿哥胤禵主持西征。後來,年羹堯果然不負眾望,屢建奇功,徹底平定了西北的戰事,也成了胤禛日後登基時,手中最重要的一張軍事王牌。
此時的允祥,手下沒有一兵一卒,卻仿佛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他曾經嚮往的「雄兵十萬」,不再是沙場上真刀真槍的士兵,而是他頭腦中那些縱橫捭闔的智慧和謀略。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但十年的幽禁,也足以讓一個人的心境徹底沉澱下來。
允祥不再是那個一笑就露出滿口白牙、意氣風發的少年了。歲月的磨礪,在他臉上刻下了風霜的痕跡,他的眼神,變得像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平靜,深邃,藏著無盡的故事。
他看透了權力的虛妄,也看透了人性的複雜。他不再為自己的冤屈而感到憤怒,也不再為失去的十年而感到遺憾。
在一個無眠的深夜,他透過高牆上那一方小小的窗口,望著天邊那輪殘月。他心裡想的,不再是自己什麼時候能出去,不再是出去後如何報復那些陷害他的人。
他在想,皇阿瑪的身體越來越差,一旦駕崩,四哥如果真的能登上那個位子,他要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國庫空虛得能跑老鼠,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腐成風,黃河連年泛濫,百姓流離失所……
這些問題,像一座座大山,壓在他的心頭。
他忽然有了一種使命感。他覺得自己這十年,並不是白白熬過來的。老天爺讓他經歷了這一切,或許就是為了讓他褪去浮躁,看清本質,好在將來,能夠幫他的四哥,撐起這片將要傾頹的江山。
他的人生目標,已經悄然間從「證明自己的清白」,升華為「輔佐兄長,實現政治抱負」。
他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和智慧,他磨礪了無比堅韌的意志。現在,他只需要靜靜地等待。
等待一個風雷激盪、石破天驚的機會。
05
康熙六十一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也特別冷。
紫禁城內外,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股不同尋常的寒意。年近七旬的康熙皇帝,在南苑行圍時偶感風寒,病情急轉直下,被移駕至京郊的暢春園休養。
消息被嚴密封鎖,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氣氛,籠罩在整個京城的上空。
八阿哥胤禩和他的黨羽們,像嗅覺靈敏的獵犬,開始了最後的瘋狂。他們的人馬在京城內外頻繁活動,與手握京城防務大權——九門提督隆科多之間的往來變得異常密切。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也是雍親王胤禛的舅舅,但他態度曖昧,誰也摸不清他到底站在哪一邊。
與此同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遙遠的西北。在那裡,康熙親封的大將軍王、十四阿哥胤禵,正手握十數萬平叛大軍。他也是皇位的有力競爭者,是八爺黨暗中倚仗的最後王牌。一旦京城有變,這支大軍隨時可能揮師東進。
身為皇四子的胤禛,表面上每日焚香沐浴,為父皇祈福,表現得至誠至孝。可實際上,他府里的心腹幕僚早已全部動員起來,像一張嚴密的蛛網,緊張地注視著京城內外的任何一絲風吹草動。
整個大清帝國的心臟,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只差一粒火星。
就在這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的時刻,暢春園裡,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旨意,從病榻上的康熙口中,虛弱地傳了出來。
「赦免……十三阿哥允祥。」
也許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這位父親終於想起了自己這個被遺忘了十年的兒子,心中有愧;也許是出於某種更深沉的政治考量,想為即將到來的亂局,投入一個誰也無法預測的變數。
沒人知道原因。
當宗人府那扇沉重的大門,在「吱呀」的刺耳聲中,被緩緩推開時,一縷蒼白的冬日陽光照了進來。允祥下意識地抬手遮住了眼睛。十年了,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如此刺眼的陽光。
來傳旨的太監跪在他面前,激動地喊著:「十三爺,大喜啊!皇上開恩,赦免您了!」
允祥扶著牆,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臉上沒有狂喜,沒有激動,甚至沒有一絲波瀾。他只是平靜地看著門外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沙啞地問了句:「皇阿瑪,身體如何了?」
太監愣了一下,才趕緊回道:「皇上……皇上在暢春園休養,宣您即刻過去覲見。」
允祥被一頂小轎,直接抬到了暢春園康熙的寢宮。
十年不見,那個曾經如山一般偉岸的父親,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虛弱地躺在病榻上,雙眼渾濁。看到允祥進來,康熙渾濁的眼中突然迸發出一絲光亮。他掙扎著伸出乾枯的手。
允祥快步上前,跪倒在床前,握住了父親那隻冰冷的手。
「皇阿瑪……」他只叫了一聲,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康熙拉著他的手,嘴唇翕動,口中喃喃不清地說著什麼,像是在道歉,又像是在託付。他那雙曾經洞察一切的眼睛裡,此刻滿是悔恨和乞求。
就在當天夜裡,一代雄主康熙皇帝,在暢春園駕崩。
喪鐘敲響,震動了整個京城。
王公大臣們被緊急召集到康熙靈前。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最關鍵的時刻,到了。
九門提督隆科多,以「顧命大臣」的身份,走上前來,當眾展開一卷黃綾,用一種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宣布了康熙皇帝的傳位遺詔:
「……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這幾句話,如同晴天霹靂,炸得八阿哥胤禩等人臉色慘白。
「不可能!」胤禩第一個站了出來,厲聲質疑,「皇阿瑪一向鍾愛十四弟,怎麼可能傳位於四哥!這遺詔是假的!」
「對!一定是矯詔!」九阿哥、十阿哥等人立刻附和。
一時間,殿內氣氛劍拔弩張,胤禩一派的官員和宗室們蠢蠢欲動,仿佛隨時都要動手。胤禛雖然有隆科多和他統領的九門兵馬支持,暫時控制住了局面,但他知道,這只是暫時的。
他面臨的第一個,也是最致命的威脅,是京城之外的兵權。
豐臺大營和西山銳健營,駐紮著數萬精銳的八旗兵馬,是拱衛京師、穩定全國局勢的關鍵力量。這支軍隊的將領,態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有傳言說,他們早已被八爺黨和十四阿哥那邊收買。
如果不能在第一時間掌控這支軍隊,一旦他們倒向胤禩,或者十四阿哥胤禵的大軍趁機發難,內外夾擊之下,他這個剛剛坐上龍椅的新君,連同整個江山,都將頃刻間分崩離析。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新君胤禛,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將目光投向了人群中那個沉默不語、剛剛走出十年牢籠的弟弟——允祥。
他的兄弟們,或在眼前虎視眈眈,或在遠方手握重兵,唯有這個弟弟,一無所有,卻也最讓他放心。
雍正沒有多餘的話,他從懷裡,顫抖著摸出了一塊令牌。那是調動豐臺大營的兵符。他快步走到允祥面前,將冰冷的兵符塞進他的手裡。
他的聲音也在顫抖,但眼神卻無比堅定:「十三弟,朕和這個江山,都交給你了。」
允祥低頭看著手裡的兵符,又抬頭看了看兄長那雙充滿血絲、飽含著信任與託付的眼睛。他沒有絲毫猶豫,十年飲冰,等的,不就是這一刻嗎?
他緊緊握住兵符,重重地點了點頭。
「臣,遵旨!」
他轉身,大步流星地走出靈堂。他換上一身早已不合身的舊戎裝,顧不上十年囚禁留下的滿身病痛,甚至來不及和剛剛團聚的家人說一句話。他只帶了身邊幾個貼身的心腹,牽過一匹快馬,翻身而上。
「駕!」
他一抖韁繩,在漆黑如墨的雪夜裡,衝出紫禁城,如一支離弦之箭,直撲城外的豐臺大營。
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他的臉上,生疼。可他感覺不到,他的心裡,只燃燒著一團火。
十年飲冰,熱血未涼!兄長的信任,大清的未來,全壓在他此行之上。成敗,就在今夜!
馬蹄踏碎了京郊雪地的寧靜。不知跑了多久,前方一片巨大的黑影,出現在了視野之中。豐臺大營,到了。
然而,迎接他們的,不是敞開的營門。
大營的轅門緊閉,吊橋高高懸起,牆上火把林立,將一排排弓箭手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
一個副將打扮的人站在高高的牆頭上,居高臨下地高聲喝問:「來者何人!深夜闖營,意欲何為!」
允祥在馬上勒住韁繩,從懷中掏出兵符,高高舉起,用盡全身力氣,沉聲喝道:「奉新君旨意,接管豐臺大營!速速開門!」
城牆上陷入了一片詭異的沉默。
片刻之後,那個副將的身邊,探出了另一個將領的頭。此人正是豐臺大營的主將,一個早已被八爺黨暗中收買的人。
他看清了下面雪地里勢單力孤的允祥,嘴角勾起一絲毫不掩飾的嘲弄和殺意。
他緩緩開口,聲音在寒夜裡傳出很遠,清晰地落入允祥和每個人的耳中:
「十三爺?您不是一直在宗人府『養病』嗎?怎麼有空到這兒來了?」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陰冷無比:「這大半夜的,風大雪大,還是請回吧。我們這裡,只認先帝和我們大將軍王十四爺的將令!」
說完,他猛地一揮手,厲聲下令:
「來人,給我……放箭!」
話音未落,城牆上響起一片「嗡」的弓弦拉滿之聲。黑暗中,無數泛著寒光的箭頭,密密麻麻地對準了雪地中那個孤獨的身影。
雍正剛剛坐上的皇位,大清未來的國運,似乎都將在這猝不及及的一陣箭雨之中,被徹底射穿,化為烏有。
06
箭在弦上,千鈞一髮。
面對城牆上那片閃著寒光的死亡森林,允祥身邊的幾個心腹臉色煞白,幾乎要撥馬而逃。
可允祥,卻穩穩地坐在馬上,一動不動。他沒有後退,反而催馬上前了一步,離那森冷的箭尖更近了。
他仰起頭,迎著牆頭上的火光,發出了一聲震徹寒夜的斷喝:「誰敢放箭!」
他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久居上位的威嚴和十年磨礪出的沉靜力量,讓牆頭上那些準備放箭的士兵,動作不由得一滯。
「睜開你們的眼睛看清楚!這是先帝御賜的兵符!見符如見君!你們是想背上一個謀逆造反、射殺皇子的千古罵名嗎?!」
他的話,字字誅心。士兵們都是吃皇糧的,造反可是要誅九族的滔天大罪。一時間,人人面面相覷,遲疑起來。
牆頭上的主將臉色一變,沒想到這個被圈禁了十年的王爺,竟還有如此氣勢。他厲聲催促道:「愣著幹什麼!給我放箭!出了事我擔著!」
就在這生死一線之際,允祥突然冷笑一聲,直視著那個主將,叫出了他的名字:「張虎,你還記不記得,康熙五十年,你在山西大同任參將時,虛報軍餉,剋扣了三萬兩銀子?這筆帳,先帝念你當時平亂有功,給你壓了下來。你以為,這事就這麼過去了嗎?」
張虎的臉色「唰」的一下變得慘白!這件事是他最大的秘密,他以為除了康熙和他自己,天底下再無第三個人知道。這個十三阿哥,是如何知道的?!
他不知道,這正是允祥在十年囚禁中,通過分析胤禛送來的那些陳年舊檔,一點點拼湊出來的「秘密武器」。
就在張虎心神大亂之際,大營之內,突然響起了幾聲吶喊。
「我等誓死效忠新皇!活捉叛將張虎!」
緊接著,營中幾個不同的方向,同時燃起了火光,傳來了兵器交擊的廝殺聲。
這正是允祥的真正後手!他被囚禁的十年,並非與世隔絕。通過胤three禛的暗中聯絡,他早已策反、團結了營中幾位出身寒微、卻因被張虎等人打壓而鬱郁不得志的中層軍官。這些人,才是他今夜敢於單騎赴險的最大底氣!
內外夾擊,軍心大亂。牆頭上的士兵們徹底慌了神,不知道該聽誰的。
張虎看著營內燃起的火光和下面神色冷峻的允祥,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他知道,他賭輸了。
「別……別放箭!」他嘶啞地喊道,「開……開營門!」
沉重的吊橋緩緩放下,轅門打開。允祥一抖韁繩,平靜地策馬而入。他經過張虎身邊時,甚至沒有多看他一眼,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拿下。」
一場足以顛覆一個王朝的兵變,就這樣被允祥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他的勝利,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他那十年間積累下來的信息、智慧和對人心的精準把握。
當允祥派人將豐臺大營的帥印和降將張虎一起送到紫禁城時,剛剛登基、還坐立不安的雍正皇帝,激動得從龍椅上站了起來。他看著這個滿身風塵、一臉疲憊卻眼神堅定的弟弟,走下御階,緊緊地抱住了他。
「十三弟,你救了朕,也救了大清!」
第二天,雍正便力排眾議,下旨冊封允祥為和碩怡親王,並且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這在清朝,是皇子親王中極少數才能獲得的無上榮耀。不僅如此,雍正還命他總理國家事務,兼管戶部——這個掌管國家錢袋子的要害部門。
允祥的人生,仿佛坐上了雲霄飛車,從一個被遺忘十年的階下囚,一步登天,成為了這個新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
然而,權力帶來的不是享受,而是沉甸甸的責任和無休止的勞碌。
允祥開始了自己短暫而輝煌的政治生涯。他深知雍正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康熙晚年政務廢弛,國庫里虧空高達數千萬兩,各級官吏貪腐成風,積重難返。
要改革,就必須得罪人。而雍正初登大寶,根基不穩,不能太過酷烈。於是,允祥主動站了出來,扮演了那個「惡人」的角色。
他一改往日與人為善的溫和性格,變得嚴厲、冷酷、不近人情。他親自主持清查全國錢糧虧空,設立「會考府」,對所有在任和離任的官員進行審計。
一時間,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被查出貪腐的官員,從巡撫、總督到小小的知縣,輕則罷官免職,重則抄家下獄。追繳虧空,更是雷厲風行,不管涉及到誰,哪怕是曾經的親朋故舊,甚至是和他沾親帶故的皇親國戚,也絕不留情。
許多過去和他關係不錯的朋友,甚至是一些看著他長大的宗室長輩,都跑到他府上,哭著喊著向他求情。
面對他們的哀求,允祥只是冷著一張臉,端著茶杯,淡淡地說:「欠了國家的錢,就得還。這是國法,誰也大不過國法。我只是奉旨辦事,也沒有辦法。」
很快,他就得了一個「鐵面王爺」的綽號。朝廷內外,無數人都在背後咒罵他,說他忘恩負負,說他心狠手辣。他把所有的罵名和怨恨,都一個人扛了下來,為雍正大刀闊斧的改革,掃清了一切障礙。
他忙得幾乎沒有一天能好好休息。常常是深夜還在戶部的衙門裡,對著堆積如山的帳冊,一筆一筆地核算;天還沒亮,又要穿上朝服,去參加冗長的早朝。
只有在單獨面對雍正的時候,允祥才會卸下那身冰冷堅硬的鎧甲。
雍正心疼他這樣不顧死活地操勞,常常在深夜裡,脫下龍袍,換上便服,親自到怡親王府,看看他的書房還亮著燈沒有,給他送去一碗御膳房熬的參湯。
「十三弟,這些髒活累活,都讓你一個人乾了,朕心裡有愧啊。」雍常不止一次這樣感嘆。
允祥總是拖著他那條越來越不靈便的傷腿,笑著說:「能為四哥分憂,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福氣。咱們兄弟,說這些就見外了。」
是啊,他們是兄弟。這份情誼,支撐著允祥走過了十年黑暗,也支撐著他在此刻,燃燒自己,照亮兄長的王朝。
但是,這燃燒,是有代價的。
十年陰冷潮濕的幽禁生活,早已摧毀了他健康的根基。那條腿的傷病越來越重,有時候疼得他連站都站不穩。再加上這般日以繼夜、殫精竭慮的繁重工作,他的身體,像一棟被掏空了地基的房子,正在迅速地垮塌下去。
他自己知道,雍正也知道。可他們都停不下來。因為他們身後,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帝國,在等著他們去拯救。
07
雍正王朝的改革,就像一艘逆水行舟的大船,而允祥,就是那最拚命的縴夫。他用自己殘存的生命力,拉著這艘船,艱難地向前。
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與時間和病魔的賽跑中度過的。
腿疾已經嚴重到讓他無法正常行走,每次上朝或出行,都需要兩個人攙扶著。雍正特許他可以坐著議政,可他每次都固執地站著,他說,君臣之禮不可廢。
即便如此,他仍然承擔著最繁重的工作。他親自抱病主持了京畿地區的水利營田事務,這是一個關係到京城數十萬百姓吃飯問題的天大工程。
他不顧醫生的勸阻和家人的哀求,親自乘坐著一輛沒有減震的簡陋馬車,顛簸在泥濘的工地上。他下了車,拄著拐杖,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田間地頭,跟那些滿身是泥的老農聊天,問他們水的流向,土的肥力。他又鑽進工匠的帳篷,和他們一起趴在圖紙上,討論著如何修建水渠,如何設置閘門。
陽光曬得他本就蒼白的臉毫無血色,但他毫不在意。他知道,百姓的飯碗,比天大。只有讓老百姓吃飽了飯,四哥的江山才能坐得穩。
除了這些具體的事務,允祥的眼光看得更遠。他深知,雍正的改革之所以推行得如此艱難,就是因為舊有的官僚體系效率低下,掣肘太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為了更高效地應對西北的戰事,允祥向雍正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建議。
他建議,在內閣之外,另設一個精幹、高效、保密性極強的核心決策機構,由皇帝直接領導,成員由最信任的幾位大臣擔任。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影響了整個清朝中後期政治格局的——軍機處。
軍機處的設立,繞開了紛繁複雜的官僚程序,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和皇權,使得皇帝的意志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貫徹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允祥拖著病體,參與了軍機處的籌建和早期運作。他是在為這個他深愛的國家,做著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頂層設計。
隨著身體一天天衰弱,他知道自己能陪兄長走的路,不多了。於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
雍正政務繁忙,對皇子們的教育時常無暇顧及。允祥便主動承擔起了教導皇四子弘曆——也就是未來的乾隆皇帝——的責任。
他不像尚書房裡那些刻板迂腐的老夫子,只會讓弘曆背誦經書。他會把年幼的弘曆接到自己的王府,帶著他去京郊的軍營,讓他看士兵們操練。他會手把手地教弘曆騎馬,教他如何張弓搭箭。
天氣好的時候,他會躺在院子裡的藤椅上,給弘曆講自己年輕時在圍場上打獵的故事,講康熙爺當年是如何排兵布陣,平定三藩的。他講的,不是書本上乾巴巴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充滿了血肉和情感的歷史。
在一個暖洋洋的午後,弘曆正在書案前練習書法,允祥靠在躺椅上,看著他,忍不住咳了幾聲。
弘曆聽見了,趕緊放下毛筆,跑到他身邊,伸出小手,有模有樣地給他捶著背。
允祥欣慰地笑了,他摸著弘曆的頭,眼神里滿是慈愛和期許,溫和地說道:「弘曆啊,記著,以後你要是做了皇帝,最要緊的一件事,不是住在多大的宮殿里,有多大的威風。最要緊的,是讓天底下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吃上飽飯,過上安穩日子。」
他喘了口氣,繼續說:「你十三叔這輩子,沒打過什麼大仗,沒立過什麼奇功,也沒什麼別的念想。就盼著,咱們大清國,能國泰民安,一年比一年好。」
這幾句樸實無華的話,像烙印一樣,深深地刻在了年幼的弘曆心中。他那時候還不太明白其中深意,只覺得這位總是滿身病痛、卻永遠對他溫和慈祥的皇叔,是一個頂好頂好的人。
雍正八年,初夏。
允祥的身體,終於走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他病倒在床,再也無法上朝。
雍正為此罷朝數日,幾乎是天天守在他的病榻前,親自端湯喂藥。他褪去了九五之尊的威嚴,就像一個普通的哥哥,看著自己即將離世的弟弟,滿臉都是無助和悲傷。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允祥的意識已經有些模糊了。他拉著雍正的手,用盡最後的力氣,氣息微弱地斷斷續續說道:
「四哥……我……我要走了……你……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別太累了……」
「弘曆……是個好孩子,將來……大清會……會更好的……」
他沒有為自己的妻子兒女求任何恩典,沒有提一句自己的功勞。他心裡想的,從始至終,都只有他的兄長和這個國家。
說完最後一句話,他那隻緊緊握著雍正的手,無力地垂了下去。
「十三弟——!」
雍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哀嚎,抱著允祥漸漸冰冷的身體,這個以冷麵鐵腕著稱的皇帝,哭得像個孩子。
怡親王允祥薨逝,年僅四十五歲。
雍正皇帝悲痛欲絕,為他舉行了清朝歷史上最高規格的葬禮。他下旨,怡親王的名號,永遠不用更換避諱字,這是有清一代,親王和臣子中絕無僅有的殊榮。他還做出了一個更驚人的決定——將允祥的牌位,配享太廟,讓他和清朝的歷代先帝一樣,接受後世子孫的祭祀。
這位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弟弟,雍正用盡了一個帝王所能給予的一切哀榮,來寄託自己無盡的哀思和感激。
08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
轉眼間,就到了乾隆中期。昔日那個跟在允祥身後捶背的少年弘曆,如今已經是在位多年的成熟君主。他勵精圖治,將父親開創的事業推向了頂峰,開創了清朝最為鼎盛的「康乾盛世」。
江山穩固,四海昇平。
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夜晚,乾隆皇帝處理完一天的奏摺,卻沒有絲毫睡意。他獨自一人來到書房,命太監取來了雍正一朝的《起居注》和一些塵封的宗人府舊檔,就著燈火,靜靜地翻閱起來。
當他讀到那些關於他十三叔怡親王允祥的記載時,不禁感慨萬千,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記憶里,十三叔總是一個面帶微笑、眼神慈祥的人,可他的臉色總是那麼蒼白,走路總要人扶著,身上似乎永遠帶著一股淡淡的藥味。
那時候,他不懂。他不懂為什麼這位權傾朝野的親王,會那麼辛苦,那麼勞累。
現在,他做了皇帝,坐在這個位子上,才真正理解了十三叔當年的不易。
他從那些發黃的檔案中,看到了允祥是如何以鐵腕手段清查虧空,為他父親充裕了國庫;他看到了允祥是如何不顧病體,奔波於水利工地,為京畿百姓換來了幾十年的安穩;他看到了十三叔是如何頂著滿朝文武的非議和咒罵,為他父親的「雍正新政」背負了所有的黑鍋。
他又從宗人府的舊檔中,一點點拼湊出了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九子奪嫡」的全部真相。
他看到了十三叔如何從一個康熙爺最寵愛的、鮮衣怒馬的少年,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他看到了十三叔在那暗無天日的十年幽禁中,是如何靠著讀書自勵,才沒有被絕望吞噬;他更看到了,在康熙駕崩那個風雨飄搖的夜晚,是他的十三叔,單人獨騎,闖入殺機四伏的豐臺大營,如何憑著過人的智慧和膽識,為自己的父親,保住了這來之不易的江山。
讀到此處,乾隆皇帝的眼眶濕潤了。
他終於徹底明白了。他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這個充裕到可以讓他六下江南的國庫,這個高效運轉到讓他可以隨心所欲的政府,這個穩定到讓他可以自詡「十全武功」的強大帝國——這所有一切的基石,正是由他那位英年早逝的十三叔,用生命、健康、名譽和無盡的血汗,一點一滴鑄就而成的。
沒有十三叔,就沒有雍正王朝的穩固;沒有雍正打下的堅實基礎,又何來他乾隆的盛世?
一股深深的感激和敬佩,從乾隆心底油然而生。
從那以後,乾隆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旨意,不斷地追封和褒獎怡親王一脈。他下令重修怡親王府,並將其改為「賢良祠」,將允祥的畫像供奉其中,讓後世子孫永遠銘記這位「賢王」的蓋世功績。
他甚至在詩作中寫道:「至今感念怡王德,誰識君臣兄弟情。」字裡行間,滿是追思。
晚年的乾隆,身為「十全老人」,大權在握,威加四海,卻時常感到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每當遇到什麼煩心事,或者是什麼難以決斷的國家大事時,他常常會屏退左右,獨自一人,來到賢良祠里。
他會站在怡親王允祥的畫像前,駐足良久。
畫像上的允祥,還是中年的模樣,面容清瘦,眼神溫潤而堅定,仿佛能看透世間一切。
乾隆會對著畫像,像個孩子對長輩傾訴一樣,輕聲地訴說著朝堂上的紛爭,訴說著兒子們的不成器,訴說著自己治理天下的疲憊和困惑。
對他而言,這位他只在童年時有過短暫相處、從未見過他治下盛世的皇叔,卻遠比朝堂上任何一位滿腹經綸的大臣,都更值得他信賴,更能讓他感到心安。
允祥這一生,從未有過登上那個至尊寶座的野心,他對那場兄弟相殘的「九子奪嫡」,自始至終都選擇了「冷眼旁觀」。他失去過恩寵,失去過自由,失去過健康,最終也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從世俗的眼光看,他似乎是個失敗者。
但他最終贏得的,是兄長毫無保留的信任,是侄兒皇帝跨越時空的敬重,是一個帝國最真摯的懷念。
在歷史那條波瀾壯闊的長河中,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為皇位斗得你死我活的兄弟們,大多都成了過眼雲煙。而他,愛新覺羅·允祥,卻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不朽。
他熬過了康熙朝的榮寵與陷落,燃盡於雍正朝的責任與犧牲,最終,在乾隆朝的追憶與榮耀中,化作了一段關於忠誠、智慧與無悔付出的永恆傳奇。
但比身體上的痛苦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絕望。
他被自己最敬愛的父親拋棄,被曾經親近的兄弟陷害,轉眼之間,就從一個天之驕子,變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階下囚。
他整日整日地面對著那四麵灰色的高牆,從最初的憤怒、不甘,到後來的茫然、麻木。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想不通自己究竟錯在了哪裡。難道自己的赤誠忠心,在權力面前,就如此一文不值嗎?
時間一天天過去,他變得越來越沉默,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他覺得自己就像院子裡那棵在秋風中凋零的枯樹,正在一點點地死去。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十三阿哥即將被世人遺忘,爛死在這高牆之內時,一道微光,卻頑強地照進了他黑暗的世界。
在所有兄弟都對他避之不及時,只有四哥胤禛,沒有忘記他。
胤禛不敢公然違抗聖意,但他冒著觸怒康熙的巨大風險,想盡了一切辦法,偷偷地幫助這個落難的弟弟。
他不能親自前來,就派了自己最心腹的老太監,隔三差五地借著送雜物的名義,給允祥送來治療腿傷的特效藥、禦寒的衣物和一些可口的飯菜。更重要的,是那些外面根本看不到的書籍。
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老太監又一次悄悄地來了。這一次,他帶來了一件厚厚的、針腳有些粗糙的黑狐皮斗篷,還有一句話。
「王爺,這是四爺讓奴才給您帶來的。」老太監壓低了聲音,「四爺說,這斗篷是他福晉帶著府里的下人,趕了好幾天才做好的,讓您一定穿上,別凍著。四爺還讓奴才給您帶句話。」
允祥接過斗篷,觸手溫暖。他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這樣的暖意了。
「四哥說什麼?」他沙啞地問。
老太監湊到他耳邊,一字一句地複述:「四爺說,天冷了,讓你務必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允祥反覆咀嚼著這句話,眼中渾濁的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
在這被全世界拋棄的時刻,還有人記得他,還在為他籌謀,還在等著他。
這句話,像一道驚雷,劈開了他心中積鬱已久的絕望和麻木,讓他瀕臨崩潰的精神重新找到了支點。他不能倒下!他若是倒下了,豈不是正中了那些害他的人的下懷?豈不是辜負了四哥的一片苦心?
從那天起,允祥變了。
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沉浸於自傷自憐。他開始冷靜地反思自己過去的一切。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失敗,在於空有一身武勇,卻不懂權謀之術;空有一片赤誠,卻不懂人心之險。
他開始利用這漫長而無所事事的幽禁時光,瘋狂地讀書。胤禛送來的每一本書,他都如饑似渴地閱讀。從經史子集,到兵法謀略,再到錢糧水利這些他過去從不關心的政務文書。
這間小小的囚室,成了他的藏經閣,他的修煉場。
十年,整整十年。
他的人雖然被困在了這方寸之地,但他的思想和眼界,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和錘鍊。他從一個只懂騎射衝鋒的「莽夫」,逐漸蛻變成了一個深諳治國之道、洞察人性的「謀士」。
他對著斑駁的牆壁,用一根小樹枝,一遍遍地推演著戰局,分析著朝政。他仿佛在為未來的某一天,做著一場漫長而周密的準備。
十年幽禁,沒有摧毀他,反而磨礪了他。他就像一把被投入烈火中反覆鍛打的寶刀,褪去了所有的雜質,只剩下最純粹的鋒芒,藏於鞘中,靜待出鞘的那一天。
04
光陰似箭,日升月落。高牆之內的日子,漫長得像是沒有盡頭。
對於外面的人來說,十三阿哥允祥已經是一個被遺忘的名字。但在這間陰冷的囚室里,允祥卻為自己開闢了一個別樣的「朝堂」。
他每天的生活,變得極其規律。天一亮,就著窗戶透進來的微光,開始讀書。那些胤禛送來的書籍,已經快被他翻爛了,書頁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他的心得和批註。沒有紙筆,他就用燒完的炭條在地上寫劃;地寫滿了,就擦掉重來。
他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了一遍又一遍,將歷朝歷代的興衰成敗、權謀得失,都刻進了自己的腦子裡。他不再僅僅把自己當成一個皇子,一個將軍,而是站在一個帝王的角度,去思考那些複雜的政務。
國庫為何會空虛?漕運為何會淤堵?鹽政的弊端在哪裡?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如何解決?
這些過去他覺得頭疼又無趣的「俗務」,現在成了他每天研究的課題。他發現,治理一個國家,遠比打贏一場戰爭要複雜得多。光有匹夫之勇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的是細緻入微的計算和長遠的規劃。
腿上的舊疾,在潮濕的環境里愈發嚴重,疼起來的時候,像是無數根針在扎骨頭,冷汗能浸濕整件衣服。但他從不呻吟一聲,只是咬緊牙關,默默忍受。他把這份疼痛,當成了對自己意志的磨礪。
有時候,為了轉移注意力,他會在地上畫出大清的疆域圖,用幾顆石子代表軍隊,反覆推演著西北邊疆的戰局,思考著如何布陣,如何運送糧草。
起初,那些奉命看守他的侍衛,都帶著一種同情和輕視的眼光看他。他們覺得這個失勢的皇子,不過是在故作姿態,用讀書來打發絕望的時光罷了。可日子久了,他們臉上的表情,漸漸變成了敬畏。
他們想不通,一個人在毫無希望的十年囚禁里,為何還能保持如此驚人的毅力和專注。他不像一個囚犯,反倒像一個閉關修煉的絕世高手。
允祥與外界唯一的聯繫,就是四哥胤禛。
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而隱秘的交流方式。胤禛每次託人送來的東西,都藏著玄機。可能是一包藥材,包藥的紙上,用米醋寫著幾個不起眼的字,風乾了看不出來,用火一烤,字跡就顯現出來;也可能是一本書,在某頁的字裡行間,用一個微小的墨點做標記,對應著一句暗語。
通過這種方式,胤禛源源不斷地將外界的信息傳遞進來。今天哪個大臣被調動了,明天某個地方發生了水災,皇阿瑪的身體狀況如何,八爺黨又有什麼新的動向……
而允祥,則成了胤禛最隱秘、最可靠的「幕後軍師」。
他身在局外,沒有了利益的糾葛,反而能把很多事情看得更通透。他會用同樣的方式,將自己的分析和建議傳遞出去。
他提醒胤禛,刑部尚書某某看似中立,實則內心早已倒向八爺黨,需多加提防;他建議胤禛,在康熙面前,要多表現出對兄弟的友愛和對政務的勤勉,但切忌功高蓋主。
康熙五十七年,西北準噶爾部再次叛亂,朝廷急需一位能征善戰的將領出征。朝堂上,各派勢力都想推舉自己的人,爭論不休。胤禛通過暗語,將幾位候選將領的名單傳給了允祥。
允祥對著這份名單,在囚室里枯坐了整整一夜。他結合自己對兵法的研究和對這幾位將領過往經歷的了解,分析了他們的派系背景、性格特點和用兵風格。第二天,他只在送出去的食盒夾層里,藏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只有三個字:「保年羹堯。」
年羹堯當時雖然只是四川巡撫,但在胤禛的極力舉薦和運作下,最終被康博任命為撫遠大將軍,代替十四阿哥胤禵主持西征。後來,年羹堯果然不負眾望,屢建奇功,徹底平定了西北的戰事,也成了胤禛日後登基時,手中最重要的一張軍事王牌。
此時的允祥,手下沒有一兵一卒,卻仿佛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他曾經嚮往的「雄兵十萬」,不再是沙場上真刀真槍的士兵,而是他頭腦中那些縱橫捭闔的智慧和謀略。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但十年的幽禁,也足以讓一個人的心境徹底沉澱下來。
允祥不再是那個一笑就露出滿口白牙、意氣風發的少年了。歲月的磨礪,在他臉上刻下了風霜的痕跡,他的眼神,變得像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平靜,深邃,藏著無盡的故事。
他看透了權力的虛妄,也看透了人性的複雜。他不再為自己的冤屈而感到憤怒,也不再為失去的十年而感到遺憾。
在一個無眠的深夜,他透過高牆上那一方小小的窗口,望著天邊那輪殘月。他心裡想的,不再是自己什麼時候能出去,不再是出去後如何報復那些陷害他的人。
他在想,皇阿瑪的身體越來越差,一旦駕崩,四哥如果真的能登上那個位子,他要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國庫空虛得能跑老鼠,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腐成風,黃河連年泛濫,百姓流離失所……
這些問題,像一座座大山,壓在他的心頭。
他忽然有了一種使命感。他覺得自己這十年,並不是白白熬過來的。老天爺讓他經歷了這一切,或許就是為了讓他褪去浮躁,看清本質,好在將來,能夠幫他的四哥,撐起這片將要傾頹的江山。
他的人生目標,已經悄然間從「證明自己的清白」,升華為「輔佐兄長,實現政治抱負」。
他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和智慧,他磨礪了無比堅韌的意志。現在,他只需要靜靜地等待。
等待一個風雷激盪、石破天驚的機會。
05
康熙六十一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也特別冷。
紫禁城內外,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股不同尋常的寒意。年近七旬的康熙皇帝,在南苑行圍時偶感風寒,病情急轉直下,被移駕至京郊的暢春園休養。
消息被嚴密封鎖,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氣氛,籠罩在整個京城的上空。
八阿哥胤禩和他的黨羽們,像嗅覺靈敏的獵犬,開始了最後的瘋狂。他們的人馬在京城內外頻繁活動,與手握京城防務大權——九門提督隆科多之間的往來變得異常密切。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也是雍親王胤禛的舅舅,但他態度曖昧,誰也摸不清他到底站在哪一邊。
與此同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遙遠的西北。在那裡,康熙親封的大將軍王、十四阿哥胤禵,正手握十數萬平叛大軍。他也是皇位的有力競爭者,是八爺黨暗中倚仗的最後王牌。一旦京城有變,這支大軍隨時可能揮師東進。
身為皇四子的胤禛,表面上每日焚香沐浴,為父皇祈福,表現得至誠至孝。可實際上,他府里的心腹幕僚早已全部動員起來,像一張嚴密的蛛網,緊張地注視著京城內外的任何一絲風吹草動。
整個大清帝國的心臟,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只差一粒火星。
就在這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的時刻,暢春園裡,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旨意,從病榻上的康熙口中,虛弱地傳了出來。
「赦免……十三阿哥允祥。」
也許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這位父親終於想起了自己這個被遺忘了十年的兒子,心中有愧;也許是出於某種更深沉的政治考量,想為即將到來的亂局,投入一個誰也無法預測的變數。
沒人知道原因。
當宗人府那扇沉重的大門,在「吱呀」的刺耳聲中,被緩緩推開時,一縷蒼白的冬日陽光照了進來。允祥下意識地抬手遮住了眼睛。十年了,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如此刺眼的陽光。
來傳旨的太監跪在他面前,激動地喊著:「十三爺,大喜啊!皇上開恩,赦免您了!」
允祥扶著牆,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臉上沒有狂喜,沒有激動,甚至沒有一絲波瀾。他只是平靜地看著門外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沙啞地問了句:「皇阿瑪,身體如何了?」
太監愣了一下,才趕緊回道:「皇上……皇上在暢春園休養,宣您即刻過去覲見。」
允祥被一頂小轎,直接抬到了暢春園康熙的寢宮。
十年不見,那個曾經如山一般偉岸的父親,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虛弱地躺在病榻上,雙眼渾濁。看到允祥進來,康熙渾濁的眼中突然迸發出一絲光亮。他掙扎著伸出乾枯的手。
允祥快步上前,跪倒在床前,握住了父親那隻冰冷的手。
「皇阿瑪……」他只叫了一聲,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康熙拉著他的手,嘴唇翕動,口中喃喃不清地說著什麼,像是在道歉,又像是在託付。他那雙曾經洞察一切的眼睛裡,此刻滿是悔恨和乞求。
就在當天夜裡,一代雄主康熙皇帝,在暢春園駕崩。
喪鐘敲響,震動了整個京城。
王公大臣們被緊急召集到康熙靈前。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最關鍵的時刻,到了。
九門提督隆科多,以「顧命大臣」的身份,走上前來,當眾展開一卷黃綾,用一種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宣布了康熙皇帝的傳位遺詔:
「……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這幾句話,如同晴天霹靂,炸得八阿哥胤禩等人臉色慘白。
「不可能!」胤禩第一個站了出來,厲聲質疑,「皇阿瑪一向鍾愛十四弟,怎麼可能傳位於四哥!這遺詔是假的!」
「對!一定是矯詔!」九阿哥、十阿哥等人立刻附和。
一時間,殿內氣氛劍拔弩張,胤禩一派的官員和宗室們蠢蠢欲動,仿佛隨時都要動手。胤禛雖然有隆科多和他統領的九門兵馬支持,暫時控制住了局面,但他知道,這只是暫時的。
他面臨的第一個,也是最致命的威脅,是京城之外的兵權。
豐臺大營和西山銳健營,駐紮著數萬精銳的八旗兵馬,是拱衛京師、穩定全國局勢的關鍵力量。這支軍隊的將領,態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有傳言說,他們早已被八爺黨和十四阿哥那邊收買。
如果不能在第一時間掌控這支軍隊,一旦他們倒向胤禩,或者十四阿哥胤禵的大軍趁機發難,內外夾擊之下,他這個剛剛坐上龍椅的新君,連同整個江山,都將頃刻間分崩離析。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新君胤禛,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將目光投向了人群中那個沉默不語、剛剛走出十年牢籠的弟弟——允祥。
他的兄弟們,或在眼前虎視眈眈,或在遠方手握重兵,唯有這個弟弟,一無所有,卻也最讓他放心。
雍正沒有多餘的話,他從懷裡,顫抖著摸出了一塊令牌。那是調動豐臺大營的兵符。他快步走到允祥面前,將冰冷的兵符塞進他的手裡。
他的聲音也在顫抖,但眼神卻無比堅定:「十三弟,朕和這個江山,都交給你了。」
允祥低頭看著手裡的兵符,又抬頭看了看兄長那雙充滿血絲、飽含著信任與託付的眼睛。他沒有絲毫猶豫,十年飲冰,等的,不就是這一刻嗎?
他緊緊握住兵符,重重地點了點頭。
「臣,遵旨!」
他轉身,大步流星地走出靈堂。他換上一身早已不合身的舊戎裝,顧不上十年囚禁留下的滿身病痛,甚至來不及和剛剛團聚的家人說一句話。他只帶了身邊幾個貼身的心腹,牽過一匹快馬,翻身而上。
「駕!」
他一抖韁繩,在漆黑如墨的雪夜裡,衝出紫禁城,如一支離弦之箭,直撲城外的豐臺大營。
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他的臉上,生疼。可他感覺不到,他的心裡,只燃燒著一團火。
十年飲冰,熱血未涼!兄長的信任,大清的未來,全壓在他此行之上。成敗,就在今夜!
馬蹄踏碎了京郊雪地的寧靜。不知跑了多久,前方一片巨大的黑影,出現在了視野之中。豐臺大營,到了。
然而,迎接他們的,不是敞開的營門。
大營的轅門緊閉,吊橋高高懸起,牆上火把林立,將一排排弓箭手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
一個副將打扮的人站在高高的牆頭上,居高臨下地高聲喝問:「來者何人!深夜闖營,意欲何為!」
允祥在馬上勒住韁繩,從懷中掏出兵符,高高舉起,用盡全身力氣,沉聲喝道:「奉新君旨意,接管豐臺大營!速速開門!」
城牆上陷入了一片詭異的沉默。
片刻之後,那個副將的身邊,探出了另一個將領的頭。此人正是豐臺大營的主將,一個早已被八爺黨暗中收買的人。
他看清了下面雪地里勢單力孤的允祥,嘴角勾起一絲毫不掩飾的嘲弄和殺意。
他緩緩開口,聲音在寒夜裡傳出很遠,清晰地落入允祥和每個人的耳中:
「十三爺?您不是一直在宗人府『養病』嗎?怎麼有空到這兒來了?」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陰冷無比:「這大半夜的,風大雪大,還是請回吧。我們這裡,只認先帝和我們大將軍王十四爺的將令!」
說完,他猛地一揮手,厲聲下令:
「來人,給我……放箭!」
話音未落,城牆上響起一片「嗡」的弓弦拉滿之聲。黑暗中,無數泛著寒光的箭頭,密密麻麻地對準了雪地中那個孤獨的身影。
雍正剛剛坐上的皇位,大清未來的國運,似乎都將在這猝不及及的一陣箭雨之中,被徹底射穿,化為烏有。
06
箭在弦上,千鈞一髮。
面對城牆上那片閃著寒光的死亡森林,允祥身邊的幾個心腹臉色煞白,幾乎要撥馬而逃。
可允祥,卻穩穩地坐在馬上,一動不動。他沒有後退,反而催馬上前了一步,離那森冷的箭尖更近了。
他仰起頭,迎著牆頭上的火光,發出了一聲震徹寒夜的斷喝:「誰敢放箭!」
他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久居上位的威嚴和十年磨礪出的沉靜力量,讓牆頭上那些準備放箭的士兵,動作不由得一滯。
「睜開你們的眼睛看清楚!這是先帝御賜的兵符!見符如見君!你們是想背上一個謀逆造反、射殺皇子的千古罵名嗎?!」
他的話,字字誅心。士兵們都是吃皇糧的,造反可是要誅九族的滔天大罪。一時間,人人面面相覷,遲疑起來。
牆頭上的主將臉色一變,沒想到這個被圈禁了十年的王爺,竟還有如此氣勢。他厲聲催促道:「愣著幹什麼!給我放箭!出了事我擔著!」
就在這生死一線之際,允祥突然冷笑一聲,直視著那個主將,叫出了他的名字:「張虎,你還記不記得,康熙五十年,你在山西大同任參將時,虛報軍餉,剋扣了三萬兩銀子?這筆帳,先帝念你當時平亂有功,給你壓了下來。你以為,這事就這麼過去了嗎?」
張虎的臉色「唰」的一下變得慘白!這件事是他最大的秘密,他以為除了康熙和他自己,天底下再無第三個人知道。這個十三阿哥,是如何知道的?!
他不知道,這正是允祥在十年囚禁中,通過分析胤禛送來的那些陳年舊檔,一點點拼湊出來的「秘密武器」。
就在張虎心神大亂之際,大營之內,突然響起了幾聲吶喊。
「我等誓死效忠新皇!活捉叛將張虎!」
緊接著,營中幾個不同的方向,同時燃起了火光,傳來了兵器交擊的廝殺聲。
這正是允祥的真正後手!他被囚禁的十年,並非與世隔絕。通過胤three禛的暗中聯絡,他早已策反、團結了營中幾位出身寒微、卻因被張虎等人打壓而鬱郁不得志的中層軍官。這些人,才是他今夜敢於單騎赴險的最大底氣!
內外夾擊,軍心大亂。牆頭上的士兵們徹底慌了神,不知道該聽誰的。
張虎看著營內燃起的火光和下面神色冷峻的允祥,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他知道,他賭輸了。
「別……別放箭!」他嘶啞地喊道,「開……開營門!」
沉重的吊橋緩緩放下,轅門打開。允祥一抖韁繩,平靜地策馬而入。他經過張虎身邊時,甚至沒有多看他一眼,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拿下。」
一場足以顛覆一個王朝的兵變,就這樣被允祥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他的勝利,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他那十年間積累下來的信息、智慧和對人心的精準把握。
當允祥派人將豐臺大營的帥印和降將張虎一起送到紫禁城時,剛剛登基、還坐立不安的雍正皇帝,激動得從龍椅上站了起來。他看著這個滿身風塵、一臉疲憊卻眼神堅定的弟弟,走下御階,緊緊地抱住了他。
「十三弟,你救了朕,也救了大清!」
第二天,雍正便力排眾議,下旨冊封允祥為和碩怡親王,並且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這在清朝,是皇子親王中極少數才能獲得的無上榮耀。不僅如此,雍正還命他總理國家事務,兼管戶部——這個掌管國家錢袋子的要害部門。
允祥的人生,仿佛坐上了雲霄飛車,從一個被遺忘十年的階下囚,一步登天,成為了這個新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
然而,權力帶來的不是享受,而是沉甸甸的責任和無休止的勞碌。
允祥開始了自己短暫而輝煌的政治生涯。他深知雍正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康熙晚年政務廢弛,國庫里虧空高達數千萬兩,各級官吏貪腐成風,積重難返。
要改革,就必須得罪人。而雍正初登大寶,根基不穩,不能太過酷烈。於是,允祥主動站了出來,扮演了那個「惡人」的角色。
他一改往日與人為善的溫和性格,變得嚴厲、冷酷、不近人情。他親自主持清查全國錢糧虧空,設立「會考府」,對所有在任和離任的官員進行審計。
一時間,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被查出貪腐的官員,從巡撫、總督到小小的知縣,輕則罷官免職,重則抄家下獄。追繳虧空,更是雷厲風行,不管涉及到誰,哪怕是曾經的親朋故舊,甚至是和他沾親帶故的皇親國戚,也絕不留情。
許多過去和他關係不錯的朋友,甚至是一些看著他長大的宗室長輩,都跑到他府上,哭著喊著向他求情。
面對他們的哀求,允祥只是冷著一張臉,端著茶杯,淡淡地說:「欠了國家的錢,就得還。這是國法,誰也大不過國法。我只是奉旨辦事,也沒有辦法。」
很快,他就得了一個「鐵面王爺」的綽號。朝廷內外,無數人都在背後咒罵他,說他忘恩負負,說他心狠手辣。他把所有的罵名和怨恨,都一個人扛了下來,為雍正大刀闊斧的改革,掃清了一切障礙。
他忙得幾乎沒有一天能好好休息。常常是深夜還在戶部的衙門裡,對著堆積如山的帳冊,一筆一筆地核算;天還沒亮,又要穿上朝服,去參加冗長的早朝。
只有在單獨面對雍正的時候,允祥才會卸下那身冰冷堅硬的鎧甲。
雍正心疼他這樣不顧死活地操勞,常常在深夜裡,脫下龍袍,換上便服,親自到怡親王府,看看他的書房還亮著燈沒有,給他送去一碗御膳房熬的參湯。
「十三弟,這些髒活累活,都讓你一個人乾了,朕心裡有愧啊。」雍常不止一次這樣感嘆。
允祥總是拖著他那條越來越不靈便的傷腿,笑著說:「能為四哥分憂,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福氣。咱們兄弟,說這些就見外了。」
是啊,他們是兄弟。這份情誼,支撐著允祥走過了十年黑暗,也支撐著他在此刻,燃燒自己,照亮兄長的王朝。
但是,這燃燒,是有代價的。
十年陰冷潮濕的幽禁生活,早已摧毀了他健康的根基。那條腿的傷病越來越重,有時候疼得他連站都站不穩。再加上這般日以繼夜、殫精竭慮的繁重工作,他的身體,像一棟被掏空了地基的房子,正在迅速地垮塌下去。
他自己知道,雍正也知道。可他們都停不下來。因為他們身後,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帝國,在等著他們去拯救。
07
雍正王朝的改革,就像一艘逆水行舟的大船,而允祥,就是那最拚命的縴夫。他用自己殘存的生命力,拉著這艘船,艱難地向前。
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與時間和病魔的賽跑中度過的。
腿疾已經嚴重到讓他無法正常行走,每次上朝或出行,都需要兩個人攙扶著。雍正特許他可以坐著議政,可他每次都固執地站著,他說,君臣之禮不可廢。
即便如此,他仍然承擔著最繁重的工作。他親自抱病主持了京畿地區的水利營田事務,這是一個關係到京城數十萬百姓吃飯問題的天大工程。
他不顧醫生的勸阻和家人的哀求,親自乘坐著一輛沒有減震的簡陋馬車,顛簸在泥濘的工地上。他下了車,拄著拐杖,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田間地頭,跟那些滿身是泥的老農聊天,問他們水的流向,土的肥力。他又鑽進工匠的帳篷,和他們一起趴在圖紙上,討論著如何修建水渠,如何設置閘門。
陽光曬得他本就蒼白的臉毫無血色,但他毫不在意。他知道,百姓的飯碗,比天大。只有讓老百姓吃飽了飯,四哥的江山才能坐得穩。
除了這些具體的事務,允祥的眼光看得更遠。他深知,雍正的改革之所以推行得如此艱難,就是因為舊有的官僚體系效率低下,掣肘太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為了更高效地應對西北的戰事,允祥向雍正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建議。
他建議,在內閣之外,另設一個精幹、高效、保密性極強的核心決策機構,由皇帝直接領導,成員由最信任的幾位大臣擔任。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影響了整個清朝中後期政治格局的——軍機處。
軍機處的設立,繞開了紛繁複雜的官僚程序,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和皇權,使得皇帝的意志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貫徹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允祥拖著病體,參與了軍機處的籌建和早期運作。他是在為這個他深愛的國家,做著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頂層設計。
隨著身體一天天衰弱,他知道自己能陪兄長走的路,不多了。於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
雍正政務繁忙,對皇子們的教育時常無暇顧及。允祥便主動承擔起了教導皇四子弘曆——也就是未來的乾隆皇帝——的責任。
他不像尚書房裡那些刻板迂腐的老夫子,只會讓弘曆背誦經書。他會把年幼的弘曆接到自己的王府,帶著他去京郊的軍營,讓他看士兵們操練。他會手把手地教弘曆騎馬,教他如何張弓搭箭。
天氣好的時候,他會躺在院子裡的藤椅上,給弘曆講自己年輕時在圍場上打獵的故事,講康熙爺當年是如何排兵布陣,平定三藩的。他講的,不是書本上乾巴巴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充滿了血肉和情感的歷史。
在一個暖洋洋的午後,弘曆正在書案前練習書法,允祥靠在躺椅上,看著他,忍不住咳了幾聲。
弘曆聽見了,趕緊放下毛筆,跑到他身邊,伸出小手,有模有樣地給他捶著背。
允祥欣慰地笑了,他摸著弘曆的頭,眼神里滿是慈愛和期許,溫和地說道:「弘曆啊,記著,以後你要是做了皇帝,最要緊的一件事,不是住在多大的宮殿里,有多大的威風。最要緊的,是讓天底下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吃上飽飯,過上安穩日子。」
他喘了口氣,繼續說:「你十三叔這輩子,沒打過什麼大仗,沒立過什麼奇功,也沒什麼別的念想。就盼著,咱們大清國,能國泰民安,一年比一年好。」
這幾句樸實無華的話,像烙印一樣,深深地刻在了年幼的弘曆心中。他那時候還不太明白其中深意,只覺得這位總是滿身病痛、卻永遠對他溫和慈祥的皇叔,是一個頂好頂好的人。
雍正八年,初夏。
允祥的身體,終於走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他病倒在床,再也無法上朝。
雍正為此罷朝數日,幾乎是天天守在他的病榻前,親自端湯喂藥。他褪去了九五之尊的威嚴,就像一個普通的哥哥,看著自己即將離世的弟弟,滿臉都是無助和悲傷。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允祥的意識已經有些模糊了。他拉著雍正的手,用盡最後的力氣,氣息微弱地斷斷續續說道:
「四哥……我……我要走了……你……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別太累了……」
「弘曆……是個好孩子,將來……大清會……會更好的……」
他沒有為自己的妻子兒女求任何恩典,沒有提一句自己的功勞。他心裡想的,從始至終,都只有他的兄長和這個國家。
說完最後一句話,他那隻緊緊握著雍正的手,無力地垂了下去。
「十三弟——!」
雍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哀嚎,抱著允祥漸漸冰冷的身體,這個以冷麵鐵腕著稱的皇帝,哭得像個孩子。
怡親王允祥薨逝,年僅四十五歲。
雍正皇帝悲痛欲絕,為他舉行了清朝歷史上最高規格的葬禮。他下旨,怡親王的名號,永遠不用更換避諱字,這是有清一代,親王和臣子中絕無僅有的殊榮。他還做出了一個更驚人的決定——將允祥的牌位,配享太廟,讓他和清朝的歷代先帝一樣,接受後世子孫的祭祀。
這位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弟弟,雍正用盡了一個帝王所能給予的一切哀榮,來寄託自己無盡的哀思和感激。
08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
轉眼間,就到了乾隆中期。昔日那個跟在允祥身後捶背的少年弘曆,如今已經是在位多年的成熟君主。他勵精圖治,將父親開創的事業推向了頂峰,開創了清朝最為鼎盛的「康乾盛世」。
江山穩固,四海昇平。
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夜晚,乾隆皇帝處理完一天的奏摺,卻沒有絲毫睡意。他獨自一人來到書房,命太監取來了雍正一朝的《起居注》和一些塵封的宗人府舊檔,就著燈火,靜靜地翻閱起來。
當他讀到那些關於他十三叔怡親王允祥的記載時,不禁感慨萬千,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記憶里,十三叔總是一個面帶微笑、眼神慈祥的人,可他的臉色總是那麼蒼白,走路總要人扶著,身上似乎永遠帶著一股淡淡的藥味。
那時候,他不懂。他不懂為什麼這位權傾朝野的親王,會那麼辛苦,那麼勞累。
現在,他做了皇帝,坐在這個位子上,才真正理解了十三叔當年的不易。
他從那些發黃的檔案中,看到了允祥是如何以鐵腕手段清查虧空,為他父親充裕了國庫;他看到了允祥是如何不顧病體,奔波於水利工地,為京畿百姓換來了幾十年的安穩;他看到了十三叔是如何頂著滿朝文武的非議和咒罵,為他父親的「雍正新政」背負了所有的黑鍋。
他又從宗人府的舊檔中,一點點拼湊出了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九子奪嫡」的全部真相。
他看到了十三叔如何從一個康熙爺最寵愛的、鮮衣怒馬的少年,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他看到了十三叔在那暗無天日的十年幽禁中,是如何靠著讀書自勵,才沒有被絕望吞噬;他更看到了,在康熙駕崩那個風雨飄搖的夜晚,是他的十三叔,單人獨騎,闖入殺機四伏的豐臺大營,如何憑著過人的智慧和膽識,為自己的父親,保住了這來之不易的江山。
讀到此處,乾隆皇帝的眼眶濕潤了。
他終於徹底明白了。他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這個充裕到可以讓他六下江南的國庫,這個高效運轉到讓他可以隨心所欲的政府,這個穩定到讓他可以自詡「十全武功」的強大帝國——這所有一切的基石,正是由他那位英年早逝的十三叔,用生命、健康、名譽和無盡的血汗,一點一滴鑄就而成的。
沒有十三叔,就沒有雍正王朝的穩固;沒有雍正打下的堅實基礎,又何來他乾隆的盛世?
一股深深的感激和敬佩,從乾隆心底油然而生。
從那以後,乾隆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旨意,不斷地追封和褒獎怡親王一脈。他下令重修怡親王府,並將其改為「賢良祠」,將允祥的畫像供奉其中,讓後世子孫永遠銘記這位「賢王」的蓋世功績。
他甚至在詩作中寫道:「至今感念怡王德,誰識君臣兄弟情。」字裡行間,滿是追思。
晚年的乾隆,身為「十全老人」,大權在握,威加四海,卻時常感到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每當遇到什麼煩心事,或者是什麼難以決斷的國家大事時,他常常會屏退左右,獨自一人,來到賢良祠里。
他會站在怡親王允祥的畫像前,駐足良久。
畫像上的允祥,還是中年的模樣,面容清瘦,眼神溫潤而堅定,仿佛能看透世間一切。
乾隆會對著畫像,像個孩子對長輩傾訴一樣,輕聲地訴說著朝堂上的紛爭,訴說著兒子們的不成器,訴說著自己治理天下的疲憊和困惑。
對他而言,這位他只在童年時有過短暫相處、從未見過他治下盛世的皇叔,卻遠比朝堂上任何一位滿腹經綸的大臣,都更值得他信賴,更能讓他感到心安。
允祥這一生,從未有過登上那個至尊寶座的野心,他對那場兄弟相殘的「九子奪嫡」,自始至終都選擇了「冷眼旁觀」。他失去過恩寵,失去過自由,失去過健康,最終也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從世俗的眼光看,他似乎是個失敗者。
但他最終贏得的,是兄長毫無保留的信任,是侄兒皇帝跨越時空的敬重,是一個帝國最真摯的懷念。
在歷史那條波瀾壯闊的長河中,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為皇位斗得你死我活的兄弟們,大多都成了過眼雲煙。而他,愛新覺羅·允祥,卻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不朽。
他熬過了康熙朝的榮寵與陷落,燃盡於雍正朝的責任與犧牲,最終,在乾隆朝的追憶與榮耀中,化作了一段關於忠誠、智慧與無悔付出的永恆傳奇。
 呂純弘 • 128K次觀看
呂純弘 • 12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