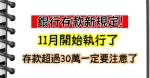3/3
下一頁
唐朝的藩鎮頑疾為何難以根除?因為您沒看到,它是歷史的進步力量

3/3
士兵們生於本地、食於本地,所有的利益都在本地,朝廷就成了一個模糊的符號,請問他對朝廷的情感維繫在哪裡?於是士兵只知上級,不知朝廷。
第三階段:朝廷與地方的割斷,怪胎髮育期
如果僅僅是中下層士兵對朝廷的忠誠度下降還好辦,麻煩的是作為藩鎮的最高統帥,他們也開始離心離德了,而導致這一惡果的無疑是李林甫的一個建議。
李林甫對唐玄宗說,咱漢人不適合當節度使,他們與朝廷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文武勾結就是個大麻煩。胡人單純,在朝廷沒利益,又善戰,好控制,所以嘛,應該節度使要用胡人,同時杜絕節度使入朝為官。
唐玄宗竟然接受了,當然,我們也不能粗暴地說李隆基糊塗,他確實也飽受漢人節度使的「折磨」。
在此之前,節度使都是從朝官中選派,如果誰的戰功突出,便可以入朝為相,此所謂「出將入相」。
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節度使們的根本利益在朝廷,出鎮對他們來說是「鍍金」,不大可能因為手上有兵權就三心二意。但隨著王忠嗣事件的爆發,以及皇甫惟明與韋堅的交接,讓唐玄宗產生了不安全感。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妙計」戳中了最脆弱的那一部分,於是以安祿山為代表,一大批胡人將領取代王忠嗣等漢將,手握邊軍大權。
與此同時,那些在中高層歷練的漢人將領們被斷送了升遷之路,甚至回歸朝廷的路。
這個格局,等於一刀斬斷了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紐帶。從那以後,藩鎮變成了獨立於朝廷而自我發育的個體,嚴重一點說,他們具備了「第二朝廷」的雛形。
第四階段:節度使土皇帝化,藩鎮化繭成蝶
客觀講,前面四個階段唐玄宗本人的責任不算大,府兵制的破產是歷史必然,本地化也是募兵制的必然結果,朝廷與藩鎮的割裂雖說不妥,也是當時現實條件的一種嘗試,算不得大罪。
唐玄宗最大的責任就在於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相反卻不斷給節度使更大的權力,以至於他們竟然成了「土皇帝」。
節度使的權限有多大,咱們以安祿山為例,此人身上的職務一大堆,平盧節度使、范陽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御史大夫、營州都督、驃騎大將軍、左僕射、閒廄群牧都使、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數不勝數。這些職務讓他除了全面掌握三鎮的軍政大權外,還兼具河北道的人事權、物資調配全,以及全國的戰馬分配權。
同時,安祿山又大耍權謀,買通了監軍、使臣,讓他擺脫了朝廷有名無實的監督,並進化為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當唐玄宗發現其中的危險時,他竟然不是修正,而是企圖靠感情牌拉攏安祿山,結果導致大廈傾危。
安史之亂後,河朔三鎮率先發難,將唐代宗、唐德宗打成了鴕鳥,以至於他們竟然上演了「四國相王」的戲碼。從那以後,藩鎮成了獨立於皇權的事實存在,並一路蔓延。
黃巢起義爆發後,藩鎮毒瘤迅速在全國擴散,即便彼時的藩鎮已經被割成了碎肉,但每一塊肉渣都沾染著毒素,無人再聽唐王朝的調遣。
第五階段:庶組階級的依附,藩鎮脫胎換骨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安史之亂後,唐代宗似乎有機會消滅藩鎮,但啟用安史亂將盤踞河朔是個巨大的失誤。不過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一則唐代宗的行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二則即便沒有河朔,藩鎮割據也是歷史的必然
前面四個階段講述的只是藩鎮顯在的發展史,但還有一條潛在的變化,那就是藩鎮的階級特性變了,成了庶組階級依附的母體,從此藩鎮脫胎換骨了。
唐朝就是一部豪門士族階級的歷史,是一群以兩京為中心的五姓七望為代表的豪門家族的歷史。這些家族被以法律的手段賦予了世代承襲的政治地位,並霸占了大唐帝國所有上層資源。
與此同時,大量的庶組階級進階無門,成了一群飽讀詩書卻只能遊走在官場門檻以外的流浪群體。
這很可怕,要知道,這些讀書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有知識、有見識、有抱負,堪稱國之棟樑,比那些靠門第出身的豪門子弟要強一百倍。您可以想像,當他們覺醒時,社會將會產生地動山搖的革命。
您可能說,大唐不是有科舉制嗎?確實有,但彼時的科舉公平性跟宋朝以後沒法比,它只是進階的入場卷之一,而不是唯一,要想入門,乃至飛黃騰達,還是要看出身。
於是這群人便開始尋找出路,竟然發現藩鎮這個獨立王國有自己的小天地,於是他們毫不猶豫地「賣身其中」。
安祿山的舉兵就跟這個人群的蠱惑煽動有很大關係,比如嚴莊、張通儒、高尚、李史魚,甚至包括安祿山的老領導張守珪的兒子張獻誠、薛仁貴的孫子薛嵩。
這些庶組階級的政治訴求很清晰,他們就是要推翻豪門集團的政治壟斷,因此他們是事實上站在了大唐帝國的對立面。
自古農民起義為何難成大事?因為沒有政治理念,而庶族階級的加盟幫藩鎮完成了質變。從那以後,藩鎮就有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驅動力。
當然,豪門集團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他們被庶組階級取代的過程歷時二百年,直到北宋建立才真正標誌著「庶組階級的春天」來了。
這樣一個生命力頑強的藩鎮集團,於大唐來說是個毒瘤,於庶組階級來說難道不是母體?於歷史的趨勢來說何嘗不是一個進步的力量?
第三階段:朝廷與地方的割斷,怪胎髮育期
如果僅僅是中下層士兵對朝廷的忠誠度下降還好辦,麻煩的是作為藩鎮的最高統帥,他們也開始離心離德了,而導致這一惡果的無疑是李林甫的一個建議。
李林甫對唐玄宗說,咱漢人不適合當節度使,他們與朝廷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文武勾結就是個大麻煩。胡人單純,在朝廷沒利益,又善戰,好控制,所以嘛,應該節度使要用胡人,同時杜絕節度使入朝為官。
唐玄宗竟然接受了,當然,我們也不能粗暴地說李隆基糊塗,他確實也飽受漢人節度使的「折磨」。
在此之前,節度使都是從朝官中選派,如果誰的戰功突出,便可以入朝為相,此所謂「出將入相」。
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節度使們的根本利益在朝廷,出鎮對他們來說是「鍍金」,不大可能因為手上有兵權就三心二意。但隨著王忠嗣事件的爆發,以及皇甫惟明與韋堅的交接,讓唐玄宗產生了不安全感。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妙計」戳中了最脆弱的那一部分,於是以安祿山為代表,一大批胡人將領取代王忠嗣等漢將,手握邊軍大權。
與此同時,那些在中高層歷練的漢人將領們被斷送了升遷之路,甚至回歸朝廷的路。
這個格局,等於一刀斬斷了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紐帶。從那以後,藩鎮變成了獨立於朝廷而自我發育的個體,嚴重一點說,他們具備了「第二朝廷」的雛形。
第四階段:節度使土皇帝化,藩鎮化繭成蝶
客觀講,前面四個階段唐玄宗本人的責任不算大,府兵制的破產是歷史必然,本地化也是募兵制的必然結果,朝廷與藩鎮的割裂雖說不妥,也是當時現實條件的一種嘗試,算不得大罪。
唐玄宗最大的責任就在於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相反卻不斷給節度使更大的權力,以至於他們竟然成了「土皇帝」。
節度使的權限有多大,咱們以安祿山為例,此人身上的職務一大堆,平盧節度使、范陽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御史大夫、營州都督、驃騎大將軍、左僕射、閒廄群牧都使、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數不勝數。這些職務讓他除了全面掌握三鎮的軍政大權外,還兼具河北道的人事權、物資調配全,以及全國的戰馬分配權。
同時,安祿山又大耍權謀,買通了監軍、使臣,讓他擺脫了朝廷有名無實的監督,並進化為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當唐玄宗發現其中的危險時,他竟然不是修正,而是企圖靠感情牌拉攏安祿山,結果導致大廈傾危。
安史之亂後,河朔三鎮率先發難,將唐代宗、唐德宗打成了鴕鳥,以至於他們竟然上演了「四國相王」的戲碼。從那以後,藩鎮成了獨立於皇權的事實存在,並一路蔓延。
黃巢起義爆發後,藩鎮毒瘤迅速在全國擴散,即便彼時的藩鎮已經被割成了碎肉,但每一塊肉渣都沾染著毒素,無人再聽唐王朝的調遣。
第五階段:庶組階級的依附,藩鎮脫胎換骨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安史之亂後,唐代宗似乎有機會消滅藩鎮,但啟用安史亂將盤踞河朔是個巨大的失誤。不過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一則唐代宗的行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二則即便沒有河朔,藩鎮割據也是歷史的必然
前面四個階段講述的只是藩鎮顯在的發展史,但還有一條潛在的變化,那就是藩鎮的階級特性變了,成了庶組階級依附的母體,從此藩鎮脫胎換骨了。
唐朝就是一部豪門士族階級的歷史,是一群以兩京為中心的五姓七望為代表的豪門家族的歷史。這些家族被以法律的手段賦予了世代承襲的政治地位,並霸占了大唐帝國所有上層資源。
與此同時,大量的庶組階級進階無門,成了一群飽讀詩書卻只能遊走在官場門檻以外的流浪群體。
這很可怕,要知道,這些讀書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有知識、有見識、有抱負,堪稱國之棟樑,比那些靠門第出身的豪門子弟要強一百倍。您可以想像,當他們覺醒時,社會將會產生地動山搖的革命。
您可能說,大唐不是有科舉制嗎?確實有,但彼時的科舉公平性跟宋朝以後沒法比,它只是進階的入場卷之一,而不是唯一,要想入門,乃至飛黃騰達,還是要看出身。
於是這群人便開始尋找出路,竟然發現藩鎮這個獨立王國有自己的小天地,於是他們毫不猶豫地「賣身其中」。
安祿山的舉兵就跟這個人群的蠱惑煽動有很大關係,比如嚴莊、張通儒、高尚、李史魚,甚至包括安祿山的老領導張守珪的兒子張獻誠、薛仁貴的孫子薛嵩。
這些庶組階級的政治訴求很清晰,他們就是要推翻豪門集團的政治壟斷,因此他們是事實上站在了大唐帝國的對立面。
自古農民起義為何難成大事?因為沒有政治理念,而庶族階級的加盟幫藩鎮完成了質變。從那以後,藩鎮就有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驅動力。
當然,豪門集團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他們被庶組階級取代的過程歷時二百年,直到北宋建立才真正標誌著「庶組階級的春天」來了。
這樣一個生命力頑強的藩鎮集團,於大唐來說是個毒瘤,於庶組階級來說難道不是母體?於歷史的趨勢來說何嘗不是一個進步的力量?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