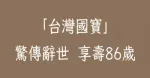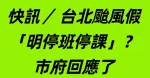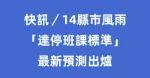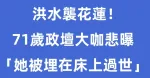2/3
下一頁
蘇軾見到友人妻子漂亮,羨慕之餘寫下一首詞,感動世人近千年

2/3
一曲終了,滿座喝彩,蘇軾亦忍不住擊節讚嘆。
王鞏更是大笑,舉杯向蘇軾致意,他本就仰慕蘇軾的才情,今日得他一句誇讚,更是欣喜。
宴席散去時,暮色已沉。
蘇軾踏著月色而歸,想起席間聽聞的只言詞組,柔奴精通醫術,常為貧苦百姓義診,她擅畫梅,筆下寒枝傲雪,風骨錚錚。
這些零碎的印象,拼湊出一個模糊卻鮮活的形象,她絕非依附於人的浮萍,而是一株在逆境中依然挺立的幽蘭。
這次邂逅,在蘇軾的記憶里不過是一段尋常的文人雅事,卻不知命運的齒輪已悄然轉動。
不久後,一場席捲朝野的政治風暴將徹底改變三人的命運,而柔奴那句尚未說出口的話,終將成為穿透千年時光的絕響。
烏台詩案
1079年的汴京城,朝堂上的暗流令人窒息。
御史台的官吏們日夜翻閱著蘇軾的詩文,字斟句酌地尋找"罪證"。
七月的一天,一隊官兵闖入湖州府衙,當眾將蘇軾押解進京。
這場震動朝野的"烏台詩案",不僅將蘇軾推向生死邊緣,更如一場颶風,席捲了與他有關的一切。
消息傳到王鞏府上時,他正在書房臨摹一幅山水。
他與蘇軾交情匪淺,書信往來頻繁,詩文唱和更是常事。
此刻他清楚地意識到,風暴將至,無人能夠獨善其身。
果然,數日後,一紙詔書將他貶至嶺南賓州,一個在當時被視為蠻荒瘴癘之地的邊陲小城。
府中頓時亂作一團,僕役們竊竊私語,眼神中滿是惶恐,幾位妾室更是哭作一團,紛紛請求離去。
王鞏沉默地坐在廳中,看著多年來積攢的字畫古籍,忽然覺得這一切如此虛幻。功名利祿如過眼雲煙,唯有大難臨頭時,才能看清人心向背。
他擺擺手,命管家給眾人分發銀兩,任由他們各自尋出路去。
就在滿府蕭索之際,一陣熟悉的腳步聲從廊外傳來。
柔奴抱著一張琵琶站在門前,"妾身已收拾好行裝,嶺南路遠,需多備些藥材。"王鞏愕然抬頭,只見她目光如水,平靜中透著不容拒絕的堅定。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賓州距汴京數千里之遙,沿途險山惡水,更有"瘴鄉"之稱。
多少貶官未能走到任所就病逝途中,即便僥倖到達,也往往因水土不服而英年早逝。
更何況柔奴並非正妻,完全可以拿著遣散銀兩,在京城另謀生路。
王鞏試圖勸阻,柔奴卻心意已決。
就在蘇軾被押往御史台大牢的同時,王鞏與柔奴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他們的馬車穿過汴京城門時,守城的士兵都投來詫異的目光,從未見過被貶官員還帶著如花美眷赴任的。
車輪碾過官道的塵土,柔奴掀開車簾回望,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歸來,但她眼中不見絲毫悔意。
遠在黃州的蘇軾聽聞此事後,在給友人的信中寫:
"定國(王鞏字)坐累遠謫,獨一女子自隨,殊為可敬。"
字裡行間滿是愧疚與欽佩。
他或許不會想到,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傳奇不止於此,三年後的重逢時刻,才是真正的千古絕唱。
嶺南歲月
嶺南的雨季總是來得猝不及防,潮濕悶熱的風裹挾著草木腐朽的氣息,鑽進簡陋的官舍每一個角落。
王鞏坐在窗前,望著檐下連綿不斷的雨簾,手中的毛筆懸在紙上,久久未能落下。
墨汁漸漸乾涸,如同他初到此地時幾近枯竭的心境。
柔奴輕手輕腳地走進來,將一碗冒著熱氣的藥湯放在案頭。
這碗藥是她按蘇軾信中寄來的方子熬制的,專門用來抵禦嶺南的瘴氣。
王鞏抬頭看她,發現她的衣袖還沾著新鮮的泥土,顯然剛從山上採藥歸來。
這個曾經在汴京錦衣玉食的歌女,如今素衣荊釵,卻比任何時候都顯得從容自在。
最初抵達賓州的日子異常艱難。
官舍破敗不堪,雨季時屋頂漏雨,冬季又四面透風。
當地百姓說著難懂的方言,看著這些北方來的"罪官"時,眼神中既有好奇,又帶著幾分疏離。
王鞏一度意志消沉,整日對著空白的宣紙發獃。
直到某個清晨,他被一陣清越的琵琶聲喚醒。
循聲望去,只見柔奴坐在院中的榕樹下,指尖在弦上輕攏慢捻,曲調竟是他當年在杭州寫就的舊詞。
音樂成了黑暗中的第一縷光。
漸漸地,柔奴不再只是彈奏王鞏的作品,她開始自己填詞譜曲。
她的詞沒有華麗辭藻,卻飽含對生活的細膩觀察,晨露未晞的稻田,雨後初晴的山巒,集市上孩童的笑語......
這些平凡景象在她的詞曲中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王鞏發現,自己筆下的墨跡也開始流動起來,那些鬱結在胸的塊壘,化作紙上酣暢淋漓的行草。
柔奴的醫術也很快在當地傳開。
她帶著藥箱走村串寨,用從陳太醫那裡學來的本事為百姓治病。
起初村民們對這個北方來的女子將信將疑,直到她治好了里正家高燒不退的小女兒。
漸漸地,"女菩薩"的名聲不脛而走。有人送來新采的草藥,有人教會她辨認嶺南特有的藥材,更有人主動幫她修繕漏雨的屋頂。
在救死扶傷的過程中,柔奴不僅治癒了他人,也在這片異鄉紮下了根。
蘇軾時常來信,除了談論詩文,更多的是分享養生之道。
他在信中詳細描述按摩腳心的方法,建議每日清晨練習,還附上食療方子,叮囑他們多吃薏米祛濕。
這些書信穿越千山萬水,成為連接三個靈魂的紐帶。
他們默契地避談朝政,只話家常,字裡行間卻流露出超越逆境的豁達,是一對尋常又不尋常的夫妻。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第二個年頭。
王鞏染上瘧疾,高燒不退。
柔奴日夜守候在榻前,用冷毛巾為他敷額,按蘇軾信中所說的方法熬制青蒿湯。
某個深夜,王鞏從昏沉中醒來,看見柔奴倚在窗邊就著月光研讀醫書,單薄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長。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這世上最動人的風景,或許不是汴京的繁華盛景,而是有人願在黑暗中為你點亮一盞燈。
三年時光如流水般逝去。
當詔令終於傳來時,王鞏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院外,聞訊而來的村民們擠滿了小路,有人捧著新摘的水果,有人拿著手織的布匹。
這些曾經陌生的面孔,如今都寫滿不舍。
離開那日,柔奴最後環顧這座簡陋的官舍。
當初他們帶著滿心惶惑而來,如今卻帶著沉甸甸的收穫離去。
北歸的路途比南來時輕鬆許多,不僅因為朝廷允許他們慢慢走,更因為心境已然不同。
而此時的蘇軾正在黃州翹首以盼......
千年絕唱
元豐六年,黃州城外,蘇軾站在渡口,望著江面上緩緩駛來的客船。
他得知王鞏北歸途經此地的消息後,早早備好了酒菜。
此刻的他既期待又忐忑,嶺南的蠻煙瘴雨,不知將故友摧折成何等模樣。
當王鞏攜著柔奴走下甲板時,蘇軾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前的王鞏非但沒有想像中的憔悴落魄,反而神采奕奕,眉宇間透著前所未有的從容。
更令人驚訝的是柔奴,三年的嶺南歲月似乎未曾在她臉上留下風霜,反而為她增添了幾分風華氣度,美麗動人。
酒過三巡,蘇軾忍不住問出那個壓在心頭多時的問題:
"嶺南荒僻,想來日子頗為艱難?"
話音未落,柔奴已輕聲接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她的聲音不大,卻如清泉擊石,在靜夜中格外清晰。
王鞏放下酒杯,笑著解釋這是他們在嶺南時常說的話,短短七個字,卻道盡了三年的風雨同舟,勝過千言萬語的傾訴。
蘇軾怔住了。
或許是為他們的愛情,或許是為他們的豁達,也或許,只是為這一刻的感動和羨慕。
他鋪開宣紙,墨汁在硯台中緩緩化開,如同心中翻湧的情感。
《定風波》的詞句如清泉般自然流淌:"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筆鋒流轉間,王鞏的才情與柔奴的靈秀躍然紙上。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這三年來,他們非但沒有被苦難壓垮,反而在相濡以沫中淬鍊出更純粹的生命光彩。
當寫到"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時,名篇已成,註定萬古流芳。
王鞏更是大笑,舉杯向蘇軾致意,他本就仰慕蘇軾的才情,今日得他一句誇讚,更是欣喜。
宴席散去時,暮色已沉。
蘇軾踏著月色而歸,想起席間聽聞的只言詞組,柔奴精通醫術,常為貧苦百姓義診,她擅畫梅,筆下寒枝傲雪,風骨錚錚。
這些零碎的印象,拼湊出一個模糊卻鮮活的形象,她絕非依附於人的浮萍,而是一株在逆境中依然挺立的幽蘭。
這次邂逅,在蘇軾的記憶里不過是一段尋常的文人雅事,卻不知命運的齒輪已悄然轉動。
不久後,一場席捲朝野的政治風暴將徹底改變三人的命運,而柔奴那句尚未說出口的話,終將成為穿透千年時光的絕響。
烏台詩案
1079年的汴京城,朝堂上的暗流令人窒息。
御史台的官吏們日夜翻閱著蘇軾的詩文,字斟句酌地尋找"罪證"。
七月的一天,一隊官兵闖入湖州府衙,當眾將蘇軾押解進京。
這場震動朝野的"烏台詩案",不僅將蘇軾推向生死邊緣,更如一場颶風,席捲了與他有關的一切。
消息傳到王鞏府上時,他正在書房臨摹一幅山水。
他與蘇軾交情匪淺,書信往來頻繁,詩文唱和更是常事。
此刻他清楚地意識到,風暴將至,無人能夠獨善其身。
果然,數日後,一紙詔書將他貶至嶺南賓州,一個在當時被視為蠻荒瘴癘之地的邊陲小城。
府中頓時亂作一團,僕役們竊竊私語,眼神中滿是惶恐,幾位妾室更是哭作一團,紛紛請求離去。
王鞏沉默地坐在廳中,看著多年來積攢的字畫古籍,忽然覺得這一切如此虛幻。功名利祿如過眼雲煙,唯有大難臨頭時,才能看清人心向背。
他擺擺手,命管家給眾人分發銀兩,任由他們各自尋出路去。
就在滿府蕭索之際,一陣熟悉的腳步聲從廊外傳來。
柔奴抱著一張琵琶站在門前,"妾身已收拾好行裝,嶺南路遠,需多備些藥材。"王鞏愕然抬頭,只見她目光如水,平靜中透著不容拒絕的堅定。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賓州距汴京數千里之遙,沿途險山惡水,更有"瘴鄉"之稱。
多少貶官未能走到任所就病逝途中,即便僥倖到達,也往往因水土不服而英年早逝。
更何況柔奴並非正妻,完全可以拿著遣散銀兩,在京城另謀生路。
王鞏試圖勸阻,柔奴卻心意已決。
就在蘇軾被押往御史台大牢的同時,王鞏與柔奴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他們的馬車穿過汴京城門時,守城的士兵都投來詫異的目光,從未見過被貶官員還帶著如花美眷赴任的。
車輪碾過官道的塵土,柔奴掀開車簾回望,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歸來,但她眼中不見絲毫悔意。
遠在黃州的蘇軾聽聞此事後,在給友人的信中寫:
"定國(王鞏字)坐累遠謫,獨一女子自隨,殊為可敬。"
字裡行間滿是愧疚與欽佩。
他或許不會想到,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傳奇不止於此,三年後的重逢時刻,才是真正的千古絕唱。
嶺南歲月
嶺南的雨季總是來得猝不及防,潮濕悶熱的風裹挾著草木腐朽的氣息,鑽進簡陋的官舍每一個角落。
王鞏坐在窗前,望著檐下連綿不斷的雨簾,手中的毛筆懸在紙上,久久未能落下。
墨汁漸漸乾涸,如同他初到此地時幾近枯竭的心境。
柔奴輕手輕腳地走進來,將一碗冒著熱氣的藥湯放在案頭。
這碗藥是她按蘇軾信中寄來的方子熬制的,專門用來抵禦嶺南的瘴氣。
王鞏抬頭看她,發現她的衣袖還沾著新鮮的泥土,顯然剛從山上採藥歸來。
這個曾經在汴京錦衣玉食的歌女,如今素衣荊釵,卻比任何時候都顯得從容自在。
最初抵達賓州的日子異常艱難。
官舍破敗不堪,雨季時屋頂漏雨,冬季又四面透風。
當地百姓說著難懂的方言,看著這些北方來的"罪官"時,眼神中既有好奇,又帶著幾分疏離。
王鞏一度意志消沉,整日對著空白的宣紙發獃。
直到某個清晨,他被一陣清越的琵琶聲喚醒。
循聲望去,只見柔奴坐在院中的榕樹下,指尖在弦上輕攏慢捻,曲調竟是他當年在杭州寫就的舊詞。
音樂成了黑暗中的第一縷光。
漸漸地,柔奴不再只是彈奏王鞏的作品,她開始自己填詞譜曲。
她的詞沒有華麗辭藻,卻飽含對生活的細膩觀察,晨露未晞的稻田,雨後初晴的山巒,集市上孩童的笑語......
這些平凡景象在她的詞曲中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王鞏發現,自己筆下的墨跡也開始流動起來,那些鬱結在胸的塊壘,化作紙上酣暢淋漓的行草。
柔奴的醫術也很快在當地傳開。
她帶著藥箱走村串寨,用從陳太醫那裡學來的本事為百姓治病。
起初村民們對這個北方來的女子將信將疑,直到她治好了里正家高燒不退的小女兒。
漸漸地,"女菩薩"的名聲不脛而走。有人送來新采的草藥,有人教會她辨認嶺南特有的藥材,更有人主動幫她修繕漏雨的屋頂。
在救死扶傷的過程中,柔奴不僅治癒了他人,也在這片異鄉紮下了根。
蘇軾時常來信,除了談論詩文,更多的是分享養生之道。
他在信中詳細描述按摩腳心的方法,建議每日清晨練習,還附上食療方子,叮囑他們多吃薏米祛濕。
這些書信穿越千山萬水,成為連接三個靈魂的紐帶。
他們默契地避談朝政,只話家常,字裡行間卻流露出超越逆境的豁達,是一對尋常又不尋常的夫妻。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第二個年頭。
王鞏染上瘧疾,高燒不退。
柔奴日夜守候在榻前,用冷毛巾為他敷額,按蘇軾信中所說的方法熬制青蒿湯。
某個深夜,王鞏從昏沉中醒來,看見柔奴倚在窗邊就著月光研讀醫書,單薄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長。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這世上最動人的風景,或許不是汴京的繁華盛景,而是有人願在黑暗中為你點亮一盞燈。
三年時光如流水般逝去。
當詔令終於傳來時,王鞏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院外,聞訊而來的村民們擠滿了小路,有人捧著新摘的水果,有人拿著手織的布匹。
這些曾經陌生的面孔,如今都寫滿不舍。
離開那日,柔奴最後環顧這座簡陋的官舍。
當初他們帶著滿心惶惑而來,如今卻帶著沉甸甸的收穫離去。
北歸的路途比南來時輕鬆許多,不僅因為朝廷允許他們慢慢走,更因為心境已然不同。
而此時的蘇軾正在黃州翹首以盼......
千年絕唱
元豐六年,黃州城外,蘇軾站在渡口,望著江面上緩緩駛來的客船。
他得知王鞏北歸途經此地的消息後,早早備好了酒菜。
此刻的他既期待又忐忑,嶺南的蠻煙瘴雨,不知將故友摧折成何等模樣。
當王鞏攜著柔奴走下甲板時,蘇軾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前的王鞏非但沒有想像中的憔悴落魄,反而神采奕奕,眉宇間透著前所未有的從容。
更令人驚訝的是柔奴,三年的嶺南歲月似乎未曾在她臉上留下風霜,反而為她增添了幾分風華氣度,美麗動人。
酒過三巡,蘇軾忍不住問出那個壓在心頭多時的問題:
"嶺南荒僻,想來日子頗為艱難?"
話音未落,柔奴已輕聲接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她的聲音不大,卻如清泉擊石,在靜夜中格外清晰。
王鞏放下酒杯,笑著解釋這是他們在嶺南時常說的話,短短七個字,卻道盡了三年的風雨同舟,勝過千言萬語的傾訴。
蘇軾怔住了。
或許是為他們的愛情,或許是為他們的豁達,也或許,只是為這一刻的感動和羨慕。
他鋪開宣紙,墨汁在硯台中緩緩化開,如同心中翻湧的情感。
《定風波》的詞句如清泉般自然流淌:"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筆鋒流轉間,王鞏的才情與柔奴的靈秀躍然紙上。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這三年來,他們非但沒有被苦難壓垮,反而在相濡以沫中淬鍊出更純粹的生命光彩。
當寫到"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時,名篇已成,註定萬古流芳。
 呂純弘 • 44K次觀看
呂純弘 • 4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16K次觀看
呂純弘 • 16K次觀看 花峰婉 • 16K次觀看
花峰婉 • 16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花峰婉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奚芝厚 • 7K次觀看
奚芝厚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滿素荷 • 3K次觀看
滿素荷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32K次觀看
喬峰傳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