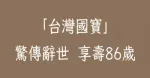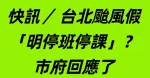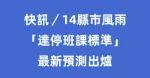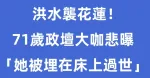4/4
下一頁
曾國藩弄死何桂清:一場教科書級別的權力鬥爭

4/4
投名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消息傳來,朝廷震怒,咸豐當即下詔將他革職,並派人將他逮捕歸案。
有時候不得不說,何桂清運氣真好。
在他逃亡租界的這段時間,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咸豐逃亡避暑山莊,對何桂清之事一時也無法顧及。
而後咸豐駕崩熱河,慈禧、奕訢又和顧命八大臣奪權,這一耽擱就是兩年多。
隨著兩宮太后和奕訢權力的穩固,自然得處理何桂清棄城之罪了。
同治元年(1862年)春,何桂清下獄。
但何桂清倒是不怎麼慌,自出逃後,就想方設法的動用自己的一切關係以減輕自己的罪名。
此前浙江巡撫王有齡、江蘇巡撫薛煥就一再為其說情,但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後又疏通禮部尚書祁寯藻、工部尚書萬青藜、御史高延祜等有分量的人物為他說話,並先後串聯了十七位大臣為其說情。
不過主審官是常州人餘光倬,對於何桂清的出逃相當憤恨,堅持要判斬立決。
這麼一來,關於如何定罪就引起了朝廷的爭論。
一方說何桂清有功勞,功過相抵,革職即可,另一方則說何桂清的罪責,按例當殺,兩派吵鬧不休,慈禧就表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
在某種成都是給何桂清一個機會,很多人就紛紛開始營救。
但本質而言,何桂清的死已經不是是否棄城,而是在於是否能夠制衡日後的湘軍。
隨著湘軍節節勝利,曾國藩的地位也水漲船高,此時的曾國藩已經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權勢一時無二,而且手上還有如狼似虎的湘軍。
一直以來,朝廷對於曾國藩和湘軍存著戒備之心,而何桂清又是一個不錯的制衡他的人選。
要是殺了何桂清,那麼還有誰能夠制衡呢?
所以恭親王奕訢和吏部尚書祁寯藻等重臣都打算給何桂清一次機會,先定「斬監侯」,後找機會救出去。
至於曾國藩,自然不希望有一個制衡自己的人出現,加上何桂清已失節,不趁機弄死他,更待何時?
於是就上疏表示:「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宜以僚屬之一言為進止;大臣以心跡定罪狀,不必以公稟之有無為權衡。」
這個表態,很有意思,奕訢他們求情,無非都死扣《大清律例》和清朝的政治傳統,打算玩人情大於法治,這是有先例的。
對於曾國藩而言,如果一昧從律法來爭辯,是爭辯不過這幫人的。
但他也不是沒有,就是用禮法道德,守城是大臣的職責,棄城就是大臣失節,何桂清棄城不守,違背讀書人和官員踐行的禮法道德,既然已經失節了,哪裡還要依從律法和人情?直接處死即可,玩了一手誅心。
奕訢和祁寯藻等重臣要求從輕發落,曾國藩要何桂清死,這讓兩宮太后面臨抉擇。
如果聽從奕訢為代表的大臣請求從輕發落,那麼兩宮太后,尤其是慈禧還未完全穩固的權威可能會受到削弱,況且慈禧和奕訢之間也存在著利益衝突。
反過來要是處死何桂清,反而可以藉機立威,使大臣和百姓臣服。
且現在是圍剿太平軍的關鍵時刻,如果拒絕曾國藩,無異於是明面打壓湘軍,所以,現在要做的是籠絡而不是打壓,就算打壓,也得平了太平軍再說。
最終在權衡之下,何桂清被判斬立決,力保何桂清的奕訢等人失敗,也預示著他們後面被奪權的命運。
可以說何桂清的死,實際上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
何桂清死後,曾國藩還送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雷霆雨露總天恩,早知報國孤忠,惟拼一死;成敗功名皆環境,既此蓋棺論定,亦足千秋。」
現在看看何桂清,算是晚清一個頗有能力的人,奈何他做大事缺乏膽氣,與人相處時又缺乏大氣,論才學和做官,都高於同時代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而且年紀輕輕,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啊,一步錯,步步錯,棄城而逃,死得不冤。
消息傳來,朝廷震怒,咸豐當即下詔將他革職,並派人將他逮捕歸案。
有時候不得不說,何桂清運氣真好。
在他逃亡租界的這段時間,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咸豐逃亡避暑山莊,對何桂清之事一時也無法顧及。
而後咸豐駕崩熱河,慈禧、奕訢又和顧命八大臣奪權,這一耽擱就是兩年多。
隨著兩宮太后和奕訢權力的穩固,自然得處理何桂清棄城之罪了。
同治元年(1862年)春,何桂清下獄。
但何桂清倒是不怎麼慌,自出逃後,就想方設法的動用自己的一切關係以減輕自己的罪名。
此前浙江巡撫王有齡、江蘇巡撫薛煥就一再為其說情,但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後又疏通禮部尚書祁寯藻、工部尚書萬青藜、御史高延祜等有分量的人物為他說話,並先後串聯了十七位大臣為其說情。
不過主審官是常州人餘光倬,對於何桂清的出逃相當憤恨,堅持要判斬立決。
這麼一來,關於如何定罪就引起了朝廷的爭論。
一方說何桂清有功勞,功過相抵,革職即可,另一方則說何桂清的罪責,按例當殺,兩派吵鬧不休,慈禧就表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
在某種成都是給何桂清一個機會,很多人就紛紛開始營救。
但本質而言,何桂清的死已經不是是否棄城,而是在於是否能夠制衡日後的湘軍。
隨著湘軍節節勝利,曾國藩的地位也水漲船高,此時的曾國藩已經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權勢一時無二,而且手上還有如狼似虎的湘軍。
一直以來,朝廷對於曾國藩和湘軍存著戒備之心,而何桂清又是一個不錯的制衡他的人選。
要是殺了何桂清,那麼還有誰能夠制衡呢?
所以恭親王奕訢和吏部尚書祁寯藻等重臣都打算給何桂清一次機會,先定「斬監侯」,後找機會救出去。
至於曾國藩,自然不希望有一個制衡自己的人出現,加上何桂清已失節,不趁機弄死他,更待何時?
於是就上疏表示:「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宜以僚屬之一言為進止;大臣以心跡定罪狀,不必以公稟之有無為權衡。」
這個表態,很有意思,奕訢他們求情,無非都死扣《大清律例》和清朝的政治傳統,打算玩人情大於法治,這是有先例的。
對於曾國藩而言,如果一昧從律法來爭辯,是爭辯不過這幫人的。
但他也不是沒有,就是用禮法道德,守城是大臣的職責,棄城就是大臣失節,何桂清棄城不守,違背讀書人和官員踐行的禮法道德,既然已經失節了,哪裡還要依從律法和人情?直接處死即可,玩了一手誅心。
奕訢和祁寯藻等重臣要求從輕發落,曾國藩要何桂清死,這讓兩宮太后面臨抉擇。
如果聽從奕訢為代表的大臣請求從輕發落,那麼兩宮太后,尤其是慈禧還未完全穩固的權威可能會受到削弱,況且慈禧和奕訢之間也存在著利益衝突。
反過來要是處死何桂清,反而可以藉機立威,使大臣和百姓臣服。
且現在是圍剿太平軍的關鍵時刻,如果拒絕曾國藩,無異於是明面打壓湘軍,所以,現在要做的是籠絡而不是打壓,就算打壓,也得平了太平軍再說。
最終在權衡之下,何桂清被判斬立決,力保何桂清的奕訢等人失敗,也預示著他們後面被奪權的命運。
可以說何桂清的死,實際上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
何桂清死後,曾國藩還送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雷霆雨露總天恩,早知報國孤忠,惟拼一死;成敗功名皆環境,既此蓋棺論定,亦足千秋。」
現在看看何桂清,算是晚清一個頗有能力的人,奈何他做大事缺乏膽氣,與人相處時又缺乏大氣,論才學和做官,都高於同時代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而且年紀輕輕,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啊,一步錯,步步錯,棄城而逃,死得不冤。
 呂純弘 • 46K次觀看
呂純弘 • 46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16K次觀看
呂純弘 • 16K次觀看 花峰婉 • 16K次觀看
花峰婉 • 16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花峰婉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奚芝厚 • 7K次觀看
奚芝厚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滿素荷 • 3K次觀看
滿素荷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32K次觀看
喬峰傳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